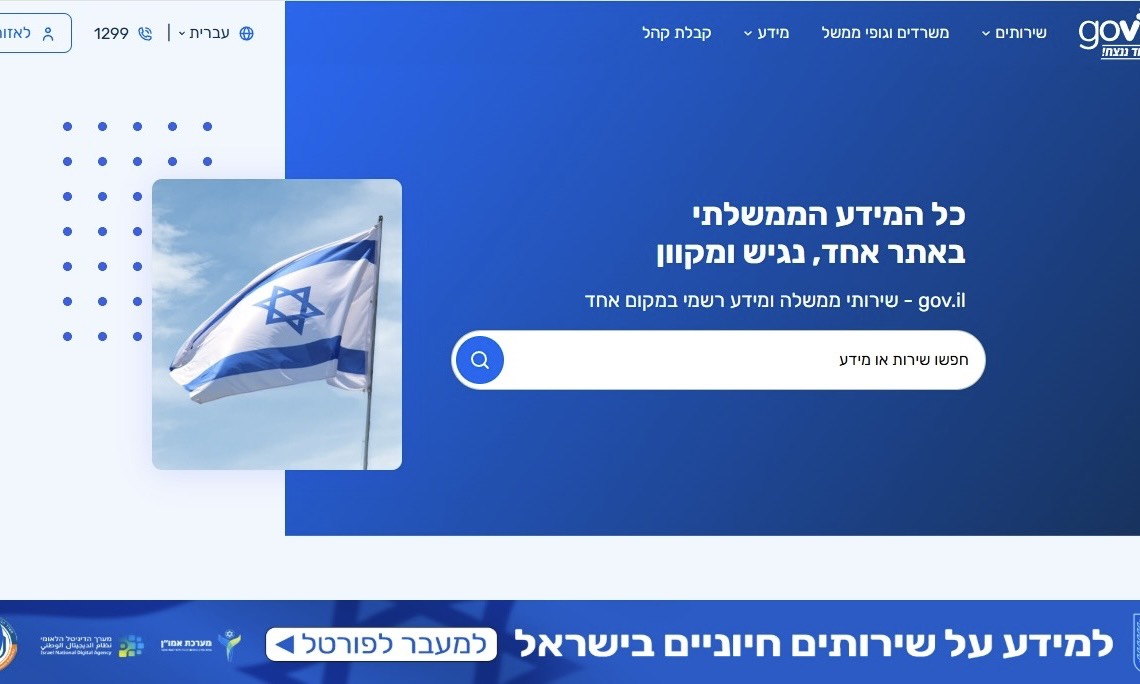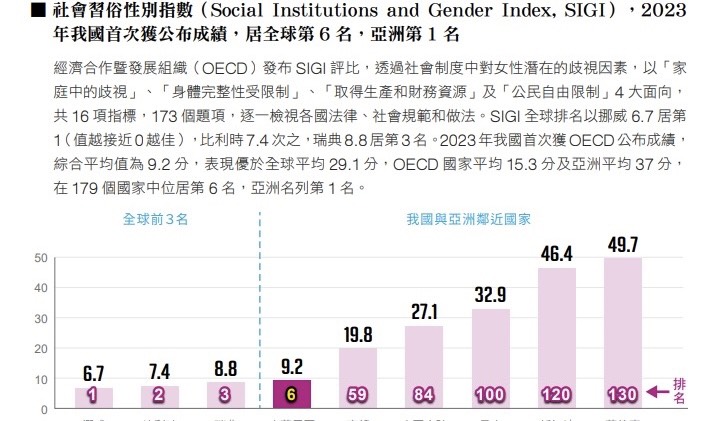【愛傳媒黃珊珊專欄】從歷史上來看,人類經歷過幾次大規模的流行病,都改變了原本社會運作的方式。其中規模最大的,就是在1918年發生的西班牙大流感。
那時的世界各國才剛剛經歷一次大戰的洗禮,這場由H1N1病毒引起的傳染病就迅速地在全球傳播,在1918至1920年之間造成全球4000萬到5000萬人死亡。這個數字,比起一次世界大戰死亡的人數還要高出一倍。各國的經濟受到巨大的波動,全球平均的GDP下降了6%,特別是原本經濟實力不強的國家更是受到巨大打擊。
西班牙大流感,其實更恰當的名稱為「1918大流行流感」,起源地其實並不在西班牙,只是因為戰爭期間,各國政府的報導並不透明,只有當時採取中立態勢的西班牙提供較公開自由的報導,才會有這樣的名稱。當時人類對大規模傳染病的應對體系尚未出現,也缺少疾病匯報的機制,政府和民間更是沒有多少公共衛生的觀念,因此在回顧這段歷史的時候,沒有太多病理學和歷史資料的紀錄。
但也是在這場全球性疾病過後,病毒學做為微生物學的重要分支快速發展,世界各國更重視公共衛生部門的建立和改善,建構傳染病報告和預防體系。特別是在當時,一些較為發達的歐美國家和蘇聯開始試著建立全民醫療保險,背後顯現的意涵是,國家提供全體國民應有的醫療保障這件事情的浮現。如果更廣一點來看,一場疫病,讓人類發現無論自己屬於哪些族群、階級、身分,每個人都應該得到全面而基本的社會力量保護。
我一直記得曾經在一篇文章看過,1918年的美國費城舉行的一場遊行,病毒是如何潛伏在人群當中,短短數十個小時內,就讓所有醫院的病床上都擠滿了感染的病患。那篇文章是由一名神父書寫,記錄了當時站到第一線不眠不休照護病患的修女回憶。在現代化的醫療體系尚未建立完全的年代,照顧窮苦病患全然是一種慈善行為,而不是一門專業的護理工作。
而當時另一座原本也要舉行遊行的城市,聖路易斯,因應報導漸增的流感新聞,取消了這場活動。一個月後,對照費城和聖路易斯兩座城市,因為流感死亡的人數,是超過一萬人和七百人的差距。這樣的案例成為後來推動社交距離概念的的實證,那些及早暫停公共活動的城市地區,在1918大流感的期間死亡率降低許多。
現在的我們已經很難想像,距離我們不過才一百年的時間,公共衛生系統建立以前,過去的醫生挨家挨戶拜訪看病的景象,以及比一次大戰死亡人數還更嚴重的疾病死亡率。從1918,到2020,一個不變的事實是,在病毒的威脅面前,只要是人,都有染病的風險。這個事實會使得人類想起:我們生活在一個共存的社會。
一個人能不能活在安全、有保障、有尊嚴的社會裡面,其實取決於每個人能不能同樣安全、有保障、有尊嚴的活在社會上。
既然疫情的問題永遠不只是公共衛生的議題這麼簡單,我們面對的難題,就永遠不只有病毒本身,更是對整個社會的體質做出一次健檢和調整。在抗疫的同時,我們如何時時刻刻關注疫情下加速擴張的社會問題?全球逐漸步入後新冠時代的現在,帶著從大疫之年復甦的抑鬱以及疲倦感,我們的社會體系,又可以怎麼做好彌補、振作、療癒的準備?
疫情之下,能夠擊垮我們的不是病毒,而是人性;然而,能夠治癒我們的,也只有人性。這是永遠不會改變的答案。
作者為前台北市副市長
照片來源:作者提供。
●更多文章見作者臉書,經授權刊載。
●專欄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