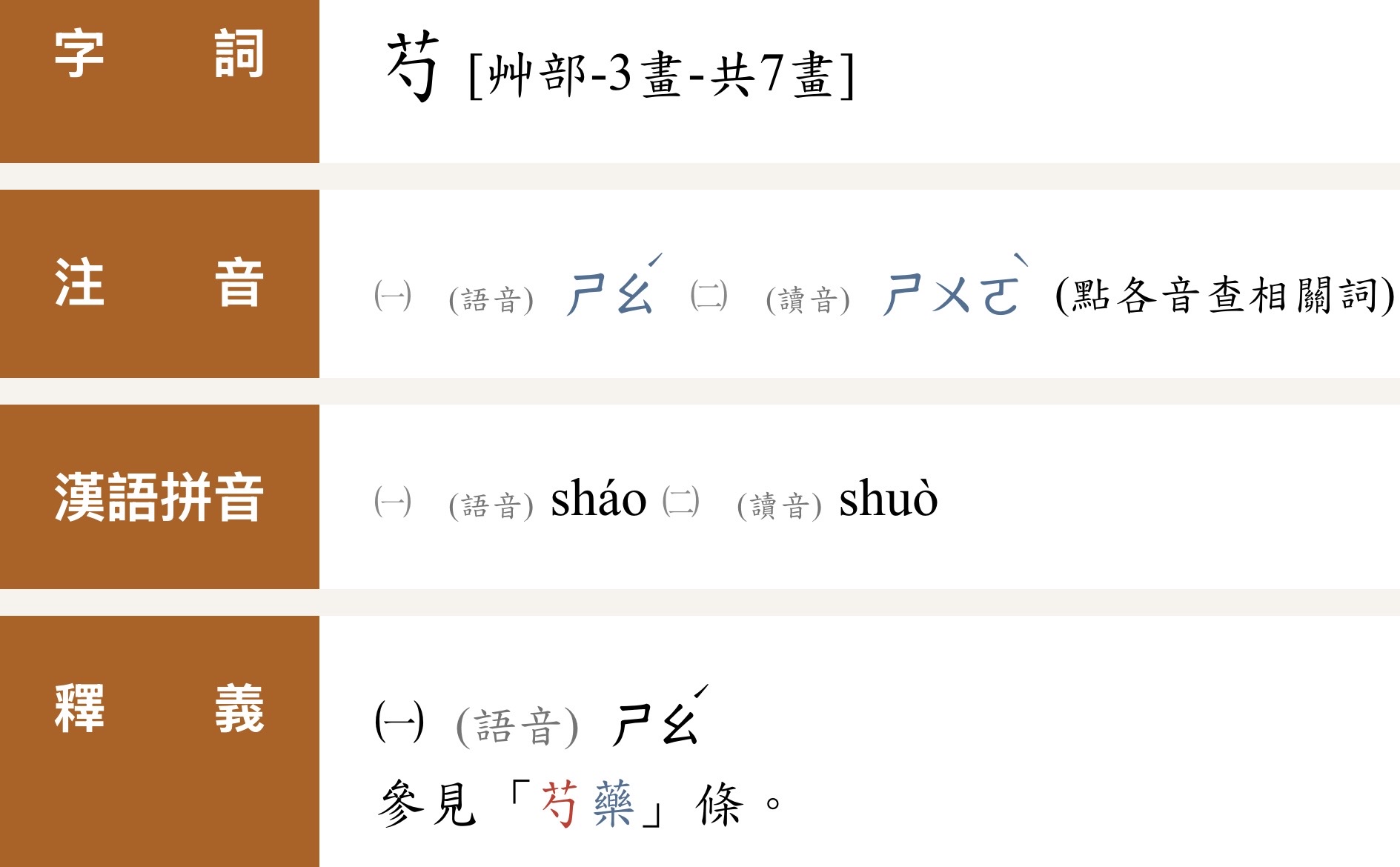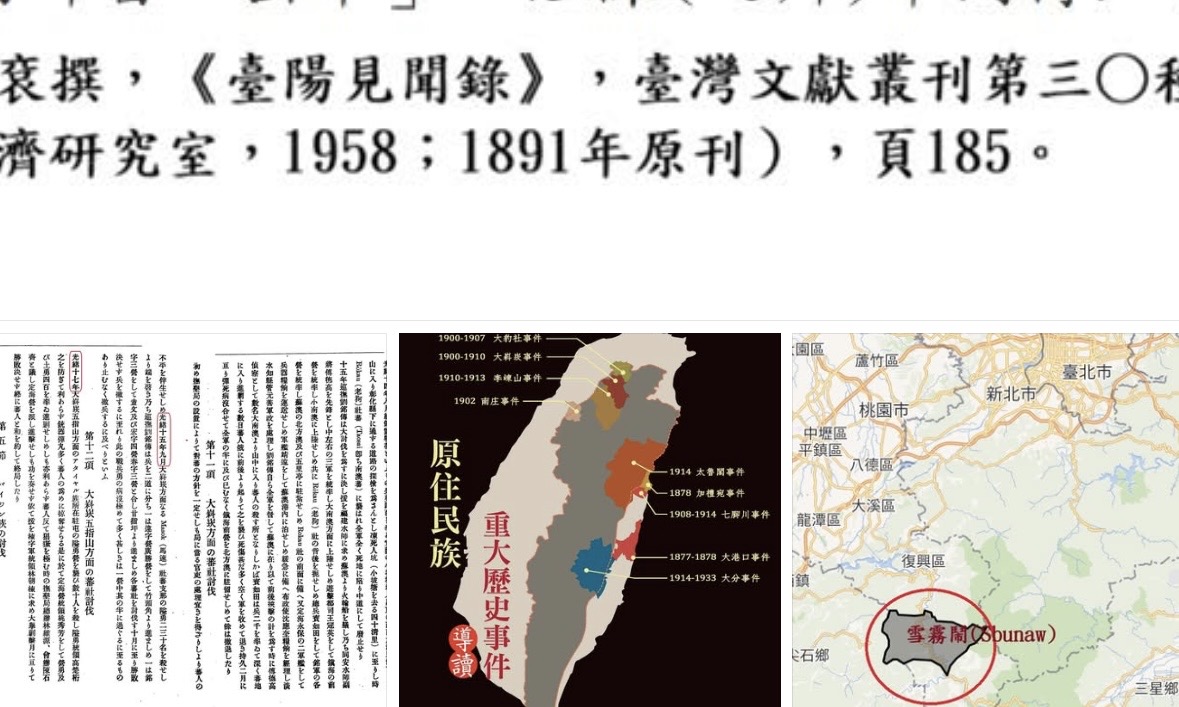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蔡詩萍專欄】結束六天日本公務出差,回到台北隔天一連串13個行程,忙得不亦樂乎。
週末清晨,讓自己喘口氣,沒去晨跑(因為明天要去拚榮耀九三馬拉松),但提醒自己:一定要寫點在京都參訪國立京都博物館那「驚鴻一瞥」的沈思者印象。
大雕塑家羅丹的《沈思者》作品,幾乎不用太多介紹了,早已是「化身為羅丹」的代表作之一。
我曾在富邦美術館近距離看過一次,很震撼,因為近距離仰看,彷彿感覺到「沈思者」張力一般的呼吸吐納,羅丹確實厲害。
這次在京都,是在戶外觀賞,距離可近,可遠,尤其有左邊看看,右邊瞧瞧,前頭望望,後邊端詳的角度與距離的調整,再加上戶外的光影變換,偶爾雲端遮日,時時陽光直視,更感覺那座沈思者,散發出獨特的沉思魅力。
《沉思者》太有名了,常常單獨被提起,致使我們常常忽略了:他原本是一系列作品中的一部分,是羅丹應邀的創作,主題是「地獄之門」,我有幸在富邦美術館的展覽場中,看到其他的「地獄之門」作品,因而有了把《沈思者》放置於較寬闊之脈絡裡理解的機會。
又由於年輕時,我稍稍翻閱過大文豪但丁的《神曲》,也對西方啟蒙主義,當代藝術略有概括性的認識,因此,那次的富邦美術館近距離觀賞羅丹,讓我彌補了未到巴黎欣賞羅丹的遺憾。
這次在京都,能在規模宏大的京都博物館看到《沈思者》矗立在館前廣場上,屹立於陽光燦燦的光影中,儘管逗留時間不算長,但我把能停留的時間幾乎都放在《沈思者》身上,相當程度的,撫慰了我這個粗淺的愛沉思的老文青靈魂。
京都博物館前的《沈思者》,我查不到關於他的鑄件編號,《沈思者》的原作當然在羅丹博物館,他的鑄件複製品相對於他的大名鼎鼎其實並不算多,但網路上查,都說數十件全尺寸複製品裡,更珍貴的,是他生前監製下的鑄件,羅丹是1917年11月17日過世的,《沉思者》的最早原創是1904年。
京都博物館在1895年正式落成,兩年後開幕,原名叫「帝國京都博物館」。
整個館的設計,我們台灣人必然眼熟,因為它的本館設計者片山東熊,專業建築,曾數度到歐美考察,他的時代明治維新,日本全心全力的脫亞入歐,向西方學習,歐式風格的建築,是那年代日本公共建設的模範,殖民台灣的日本同樣也把它引進到了台灣。
當時的京都博物館,全心全意的模仿歐洲,在典雅恢弘的主體建築前,一池噴泉,後面矗立羅丹的《沈思者》,固然可能是歐風東漸的時髦風,但若稍知《沈思者》獨特的造型,與羅丹受到但丁的啟發,就可能不會完全從歐風東漸這麼簡單的角度去了解了。
從帝國京都博物館設立的年代與它的建築布局巧思,我推測:這件《沈思者》鑄件極有可能是羅丹生前親自監督製作的。
《沈思者》最引人,最動人之處,是他獨特的姿態,體型巨魄,肌肉糾結,呈現了西方自希臘羅馬時代以來,對身體美的傳承。
但《沈思者》以右手肘置放於左膝蓋上,以右手掌背撐起下顎「毫不輕鬆」的坐姿去沉思的姿態,以及面部的痛苦,腳趾的盤曲使力,都讓我們觀賞者能清晰感受到他「沉思的張力」、「思索的深邃」,以及「對未知的隱憂」。
這是但丁的《神曲》生命探索,這也是羅丹在(舊)世紀末(新)世紀初對「現代」的思索,儘管呼應了他們兩人不同時代的課題,卻由於文學與藝術手法的精湛,讓穿越時代的後代的我們,依舊能感受《沈思者》的宿命,思索者的堅毅。
十九世紀末,日本的維新是走在中國之前的,但從那之後,日本漸漸也步入了軍國主義的單行道,步入自己踏進西方列強殖民主義的覆轍。
現在回眸往昔,看看國立京都博物館前的《沈思者》雕像,或許才明白羅丹的了不起,或許才明白沉思之不易的真正意義吧!
作者為知名作家、台北市文化局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