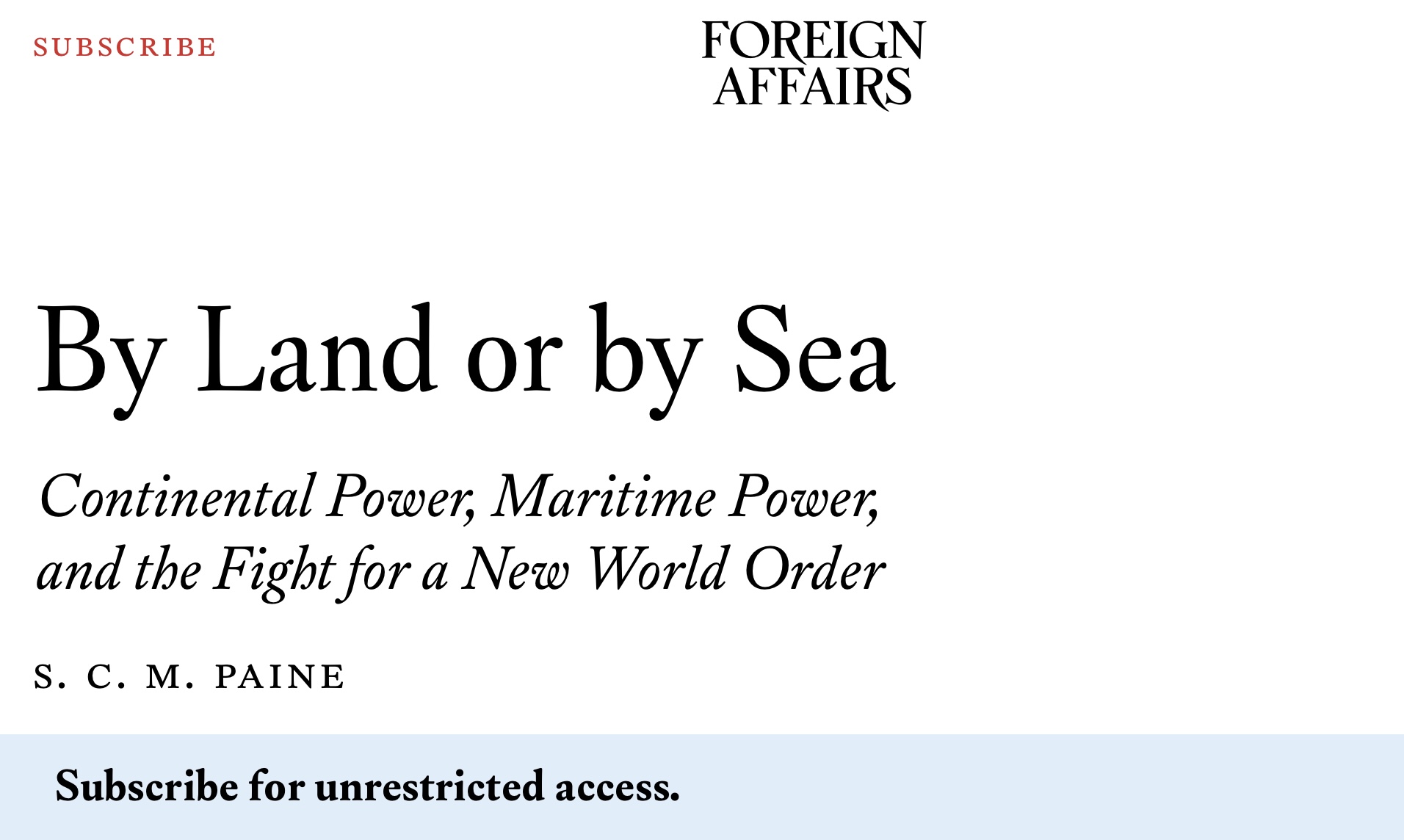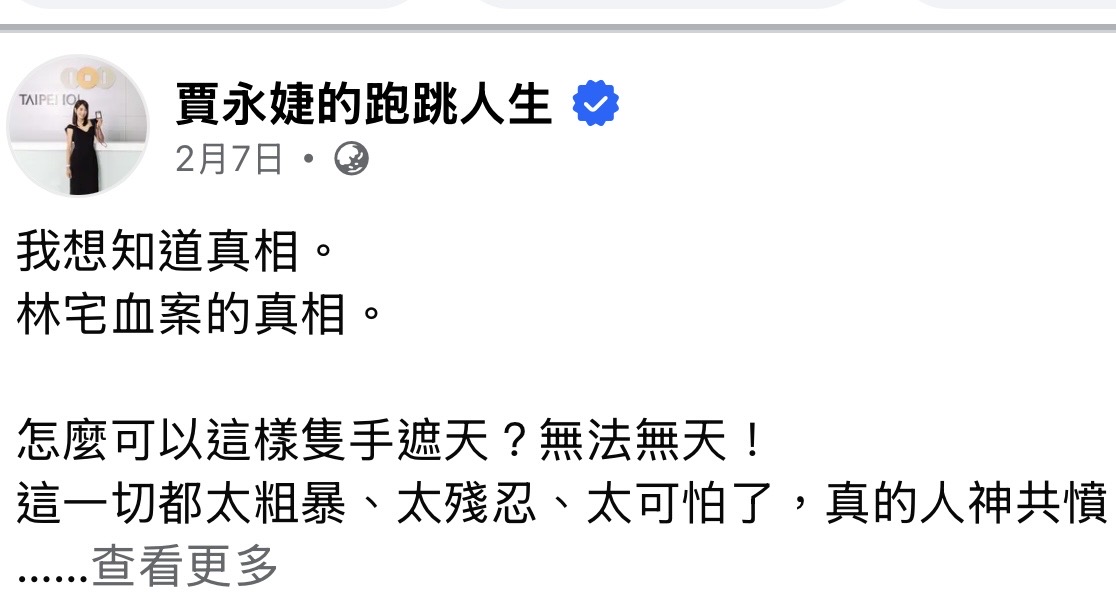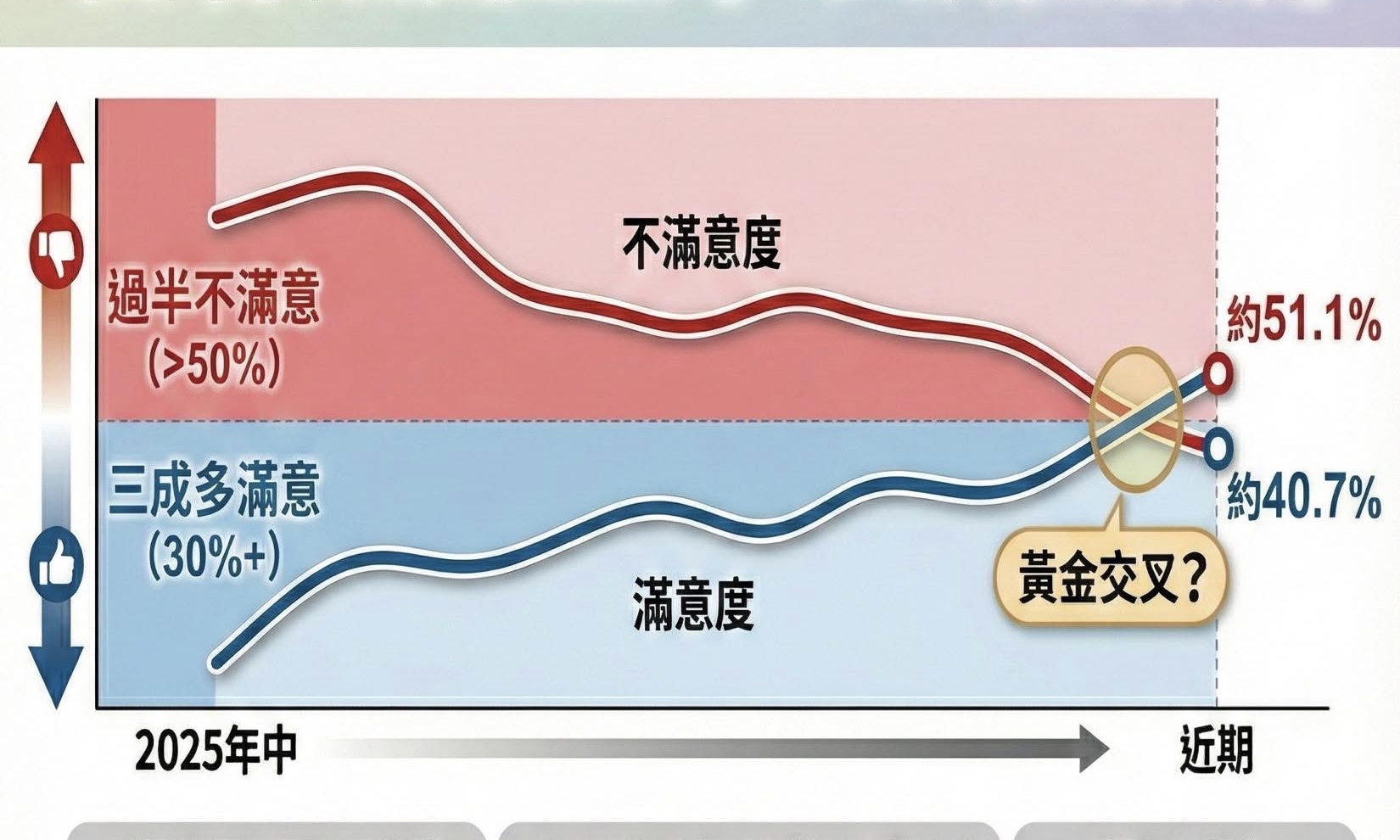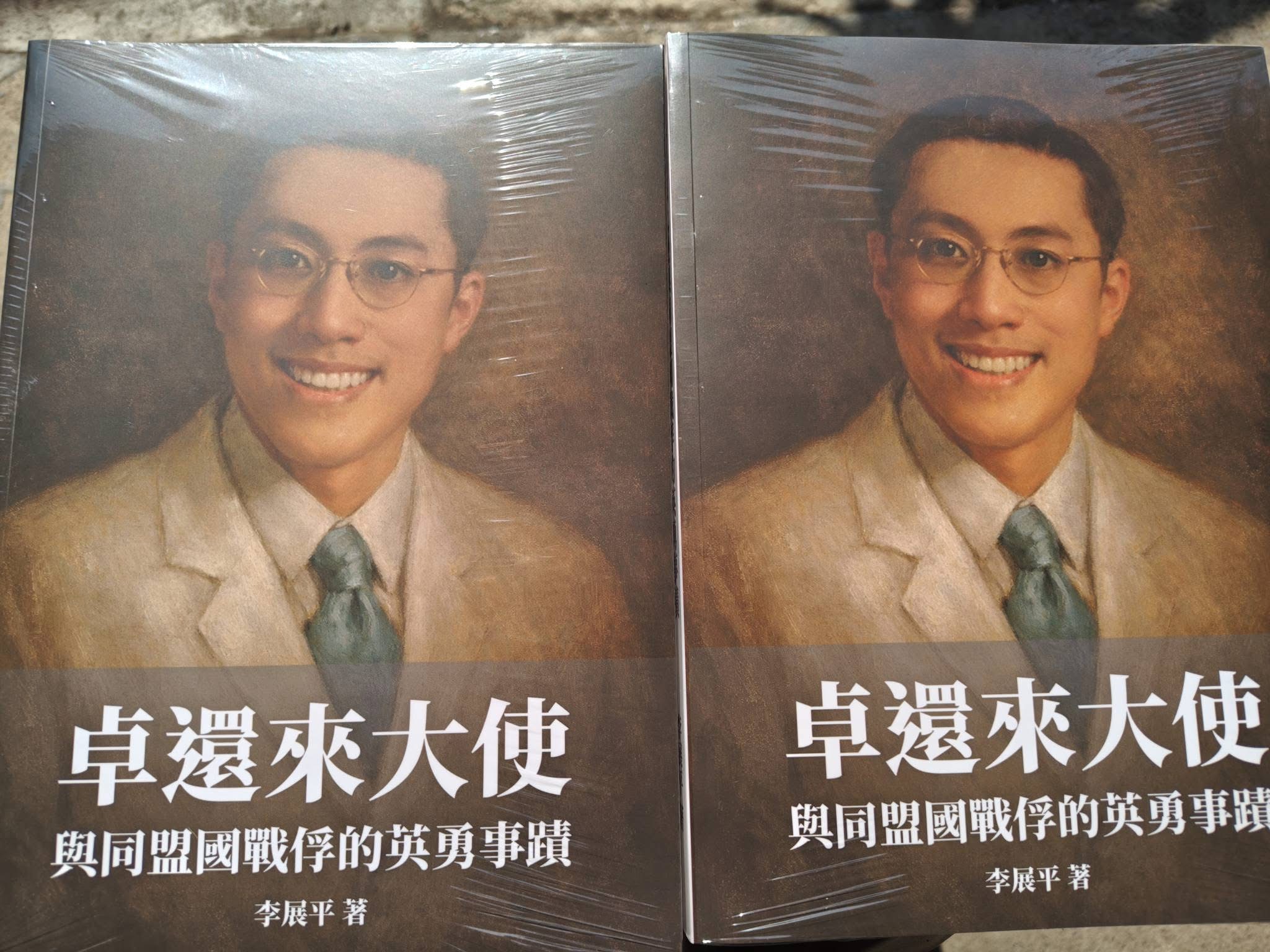照片為《外交事務》官網截圖
【聚傳媒上官亂文章】前幾天《外交事務》發布文章〈陸路或海路,大陸強國、海上強國和新世界秩序之爭〉。這不禁讓人想到, “台灣是一個海洋文明的國家”這也是民進黨和泛绿知识分子長期以來反覆強調的論述。它不僅是政治口號,更是一種“主體”敘事:借由“海洋”象征開放、包容與多元,來與“大陸”所象征的封閉、集權與暴力形成對照,同時與抗中敘事合流。在這種修辭邏輯中,台灣被塑造成東亞民主的燈塔,一個以海洋精神為依歸、拒絕大陸傳統的現代化島嶼。
然而,若從歷史與社會文化的脈絡回溯,這種文明自我定位的邏輯並不穩固。台灣確實四面環海,但它的制度結構、社會文化乃至集體心理,更多地呈現出一種混雜形態:既承襲了大陸儒家傳統與威權遺緒,又未真正發展出典型“海洋文明”應有的法治精神與開放格局。換言之,所謂的“海洋文明”,在台灣更多是一種政治想象,而非社會現實。
海洋與大陸的二元对立神話
“海洋文明”與“大陸文明”的對立,最早並非來自台灣,而是源於歐洲近代地緣政治的範式——尤其體現在英國與歐洲大陸的長期競爭之中。英國歷史學家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曾提出“世界島”與“心臟地帶”理論,他擔憂英國這個海洋強權以及世界的自由將會受到陸權的威脅;而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則從關切權力平衡的角度說明美國企圖以海洋阻隔敵人的孤立主義政策必敗,想成功,就必須確保歐亞大陸區域之中不會出現強權,也因此被稱為“圍堵政策教父”。這一地緣辯證關系在冷戰時期被美國繼承,用以構建“自由世界”與“專制大陸”的對立敘事。
外交事務前段時間的長文《陸路或海路,大陸強國、海上強國和新世界秩序之爭》似乎在支持這個觀點,但是,和麥氏與斯氏一樣,該理論出現了典型的海洋與大陸的二元對立神話,就是:假設地理形態(是否靠海)決定了國家性格與戰略文化,即“大陸=暴力、擴張、零和;海洋=規則、合作、共贏。”這個理論也的確被台灣的泛綠學界引用,但是這個理論忽略了現實中地理、制度、歷史之間的覆雜互動。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日本。日本作為島國,其地理條件極“海洋”:四面環海、貿易依存度高;擁有強大的海軍傳統;戰前也是一個高度工業化的開放經濟體。但在20世紀前半葉,日本的擴張主義和納粹德國沒有本質差別——它發動了東亞的戰爭,並襲擊珍珠港。日本當時的軍國主義本質上是模仿歐洲大陸帝國的模式(普魯士式軍制與民族主義),因此雖是島國,卻行為上完全是“大陸國家”。這恰好說明“海洋地理”並不能阻止“大陸心態”。
反過來也成立。
英國與美國也並非“素來和平的海洋文明”,作者理想化了“基於規則的海洋秩序”,但忽略了其建立過程中的暴力與排他性。英國的“海洋秩序”是通過奴隸貿易、殖民掠奪和炮艦外交建立的。美國的全球地位,也是在美西戰爭、越南戰爭等一系列擴張中鞏固的。這類戰爭並非“例外”,而是海洋帝國通過規則與暴力結合維持秩序的常態。
海洋文明神話的“規則秩序”,本質上是一種意識形態裝置,這些看起來普惠性的規則雖然是二戰後美國及其盟友制定的,但一旦規則不利於美國,它也會單方面退出(巴黎協定等),因此,“基於規則”在國際關系中其實是一種合法性話術:海洋國家的自我正當化敘事,用來掩蓋權力結構的不對稱。
另外,“海洋文明=開放與貿易”的邏輯忽略了經濟全球化的雙刃性,海洋文明依賴貿易與資本流動,但這種全球化同樣會擴大國內階級差距,導致產業外移、民粹崛起,最終反噬海洋國家自身。美國目前遇到的問題並非“偏離海洋精神”,而正是“海洋秩序的副作用回流本土”。
而且,海洋國家和大陸國家也會在不同歷史時期互相“漂移”:美國在19世紀是典型的大陸國家(向西擴張、征服印第安人);蘇聯在赫魯曉夫時期嘗試海軍化。
所以綜合來說,一個國家能否維持和平與開放,取決於制度、文化與戰略理性的互動,而不是地圖上的顏色。
台灣是不是海洋文明?
這種理論在冷戰後的台灣政治語境中被重新包裝:大陸成為威權、僵化與同質的象征;海洋則被賦予民主、多元與自由的價值。那麽說回台灣,那麽台灣是不是海洋文明?
簡單回答是:台灣社會文化在本質上仍然是“大陸文明的延續體”,而“海洋文明”在台灣更多是一種政治修辭、意識形態象征,而非社會現實。台灣政界所援引的“海洋文明論”,其實更多是一種“政治修辭的地緣學”,而非真正的社會科學概念。
我們可以分成五個分析層面來看——歷史結構、文化底層、政治制度、社會結構與移民政策。
首先,台灣的歷史結構,其實是從海盜島到殖民島。早期的台灣海域確實存在著典型的“海洋文化”——明鄭時期的鄭氏王國與南中國海的海盜網絡,構成了一種流動、貿易與掠奪交織的文化生態。然而,這種“海洋文明”並非現代意義下的民主與開放,而更接近一種邊緣的生存經濟,帶有濃厚的掠奪性與封閉性。
清朝治理台灣後,中央集權的行政制度與儒家禮制迅速覆蓋了原有的地方自治傳統。日本殖民時期,台灣雖經歷現代化,但也深受日本的帝國治理邏輯影響——強調秩序、紀律與國家效率,台灣人在社會中多屬於服從角色。戰後,國民黨政權延續了這一體制,以威權與儒家式的道德治理構築國家機器。
由此可見,台灣的政治制度與社會組織方式,主要承襲自“大陸型的國家邏輯”與“外來殖民的治理理性”,而非“海洋式的契約與自治傳統”。
即使在民主化之後,這種制度慣性仍然存在。台灣的官僚體系高度中央集權,地方自治權有限,社會動員多以政黨或派系為核心,公民自治團體也和政黨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兩次大罷免運動即是例證)。這些特征都更接近大陸文明的“組織型社會”,而非海洋文明的“契約型社會”。
從文化底層來看,台灣是典型的大陸型儒家倫理與“閩粵鄉土文化”秩序社會,在家庭倫理上:重家族、重長幼、講“聽話”“孝順”“顧面子”,這都是儒家文化的倫理核心。教育觀念上,崇尚學歷、考試導向、服從權威。這些並非源自“海洋文明”的個人主義、契約精神、獨立思考,而是典型的東亞大陸心態。即便民主體制下的台灣人熱衷於表達意見,他們表達的方式和背後的心理邏輯仍是“群體取向”,而非“個體自主”。
另外,“閩粵文化”強化了“地方宗族性”,而非開放性。台灣的閩南文化源於福建沿海,但福建的社會本身是“沿海的大陸文化”——它不是開放的商幫文化,而是以宗族、廟宇、地方派系為核心的社會。
因此也影響到台灣的地方政治、人情網絡、信仰體系(媽祖廟、王爺廟),其實都強化了地方與內部互惠機制;這種社會結構在民主化後延續為“派系政治”“人情選舉”“宗教動員”。
同理,在政治制度方面,雖然台灣形式上半總統制,實質上延續中央集權與道德政治。
台灣表面是“海洋國家式的民主”,但內部運作仍體現“大陸文明的政治邏輯”:政黨結構是領袖崇拜型而非制度型;權力高度集中在行政體系與黨機器;政治動員訴諸情感與道德正當性(如“保衛民主”、“國家安全”),而非契約性協商。比如陸配的污名化,就嚴重依賴情緒訴諸正當性,和事實無關。
社會結構上,雖然台灣公民社會發達,社群緊密,但總體來說相對封閉。輿論雖然活躍,言論相對自由,但同溫層明顯,兩極化嚴重,理性討論空間被急劇壓縮。意識形態“同溫層”極深,不同立場之間缺乏對話機制;網絡輿論空間表現為“群體攻擊”“道德排除”,這是一種大陸式社會的道德共同體心態,而非“海洋式公共理性”。
社會輿論中常見的“情緒政治”“道德審判”“網絡獵巫”,正體現出台灣公共文化中“群體情感優先於制度理性”的特征,甚至顯現出獨特的“道德民粹結構”。這與民進黨所宣稱的“海洋式理性協商”相去甚遠。
在移民政策上,則是明顯的封閉、道德化、不確定性、身份本位。台灣的移民政策與其所宣稱的“開放國際化”形成鮮明反差。對東南亞、陸配、外籍勞工嚴格設限、歧視性語言普遍存在;對歐美日移民則以“高階專業人才”歡迎,形成明顯的“文化等級制度”;入籍門檻高、審查繁瑣、政治權利獲取極慢。這與典型海洋文明(如加拿大、澳大利亞、英國)“以制度認同替代血緣認同”的移民邏輯完全相反。
尤其是當執政黨開始擴大抗中保台敘事之後,移民政策就存在各種問題:包括回溯性審查(對1.2萬名陸配進行回溯性的行政審查),缺乏證據門檻的指控,違反中立適用(同一套規則並未對所有外國配偶都等比例適用),對陸配的懲罰和指控未匹配具體的風險行為,亦不符合比例原則(安全政策的具體預期收益和對陸配基本權利的剝奪不相稱),缺乏可預測性(對陸配權益的政令存在溯及既往、陸配身分政策有頻繁變動之輿),缺乏日落條款和覆核機制(落日條款即保證在風險時期度過之後,該族群還能恢復合法權益)……
台灣的“開放”往往是選擇性的:對友善的外來者開放,對威脅其政治認同的群體則表現出排斥與防御。由此可見,目前台灣的移民邏輯其實是:“血統+政治忠誠”的大陸型身份制度,只是換了一個“自由民主”的話語外殼。
從“文明定位”到“文明實踐”:重新思考台灣的定位
綜合上述脈絡,台灣社會在文明結構上既非純粹的大陸型,也非真正的海洋型,而是一種“中間文明”或“過渡型社會”。其核心特征是:在地理上屬於海洋,在制度與文化上仍屬大陸遺緒;在政治理念上追求開放,但在社會實踐上又依循熟人網絡與情感秩序。
這種矛盾結構既造就了台灣的活力,也限制了它的成熟。台灣的民主化並非基於契約精神與公民社會的自發成長,而是威權體制逐步松動後的政治妥協。這種民主雖然形式完善,但在文化上仍帶有“集體道德統治”的特征。因而,當台灣以“海洋文明”自居時,它事實上是在以象征性話語掩飾自身的結構性矛盾。
但是,真正的問題並不在於台灣究竟屬於哪一種文明,而在於它如何在文明的張力中確立自身的主體性。文明不是地理決定的,而是制度與文化的實踐結果。一個社會能否開放,不在於它是否面向海洋,而在於它能否容納異己、保障法治、承認多元。
如果台灣要實現其所宣稱的“海洋文明”,關鍵不在對大陸文明的否定,而在於超越自身的排他性與情緒政治,建立以制度為基礎的社會信任與法治秩序。否則,所謂“海洋”,將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幻象;而“大陸的影子”,將繼續潛伏在台灣社會的每一處制度縫隙之中。
台灣的文明身份是一面鏡子。它映照出東亞現代性中的共同困境:在傳統與現代、情感與理性、身份與開放之間的拉扯。“海洋文明”或“大陸文明”只是敘事工具,而非終極定義。真正的文明,不在於自我標榜的象征,而在於面對自身矛盾的誠實。
今日的台灣,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海洋修辭”,而是對自身歷史與文化的深度反思。唯有承認自己既有海洋的漂泊,也有大陸的重量,台灣或許才能在文明的邊界上,找到真正的身份定位。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投稿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