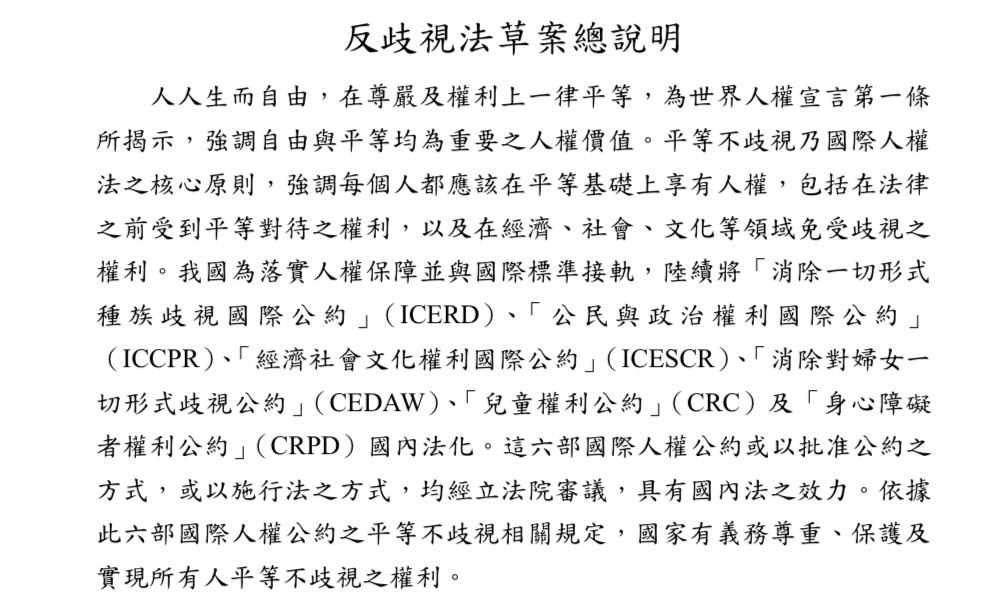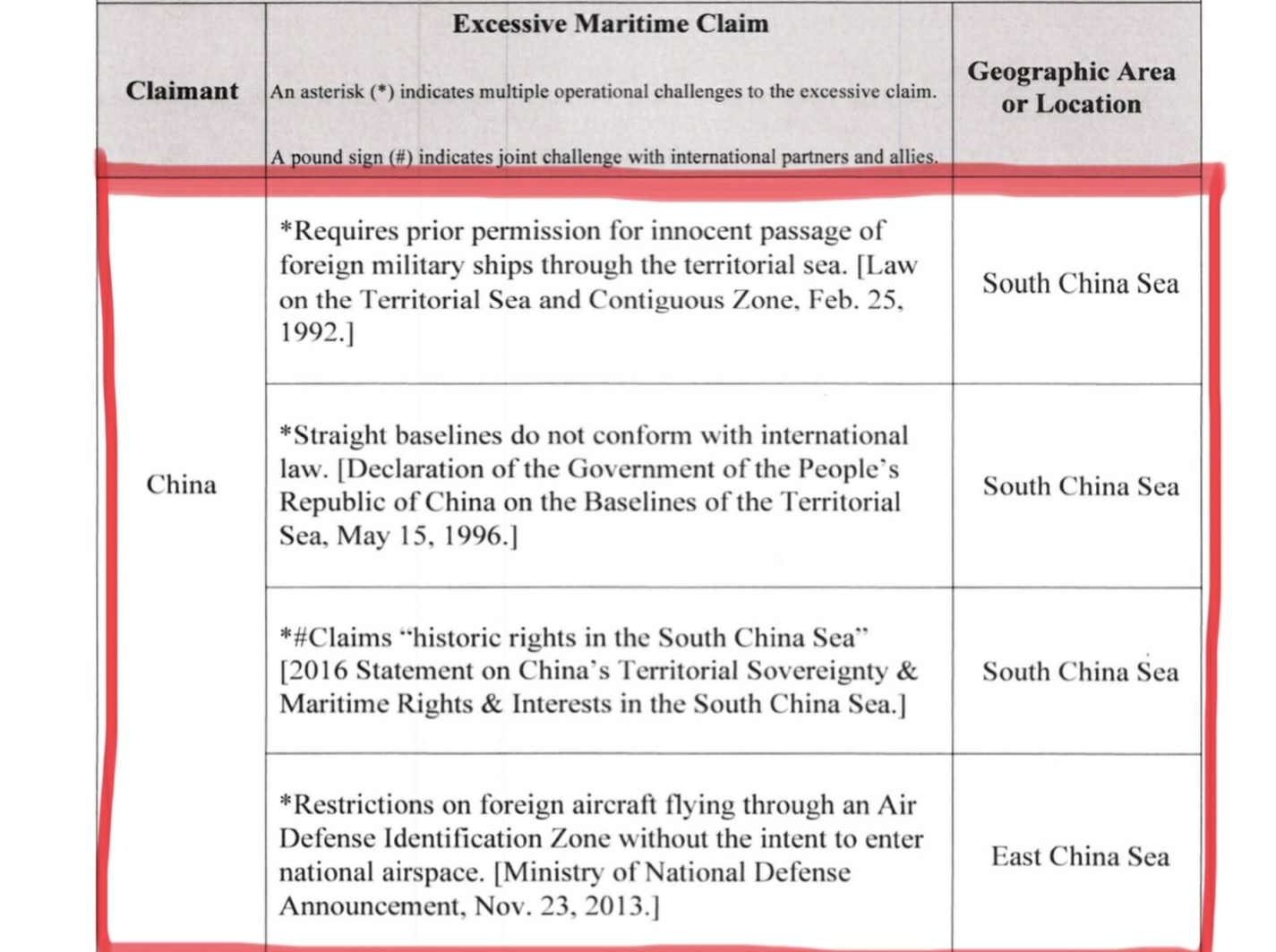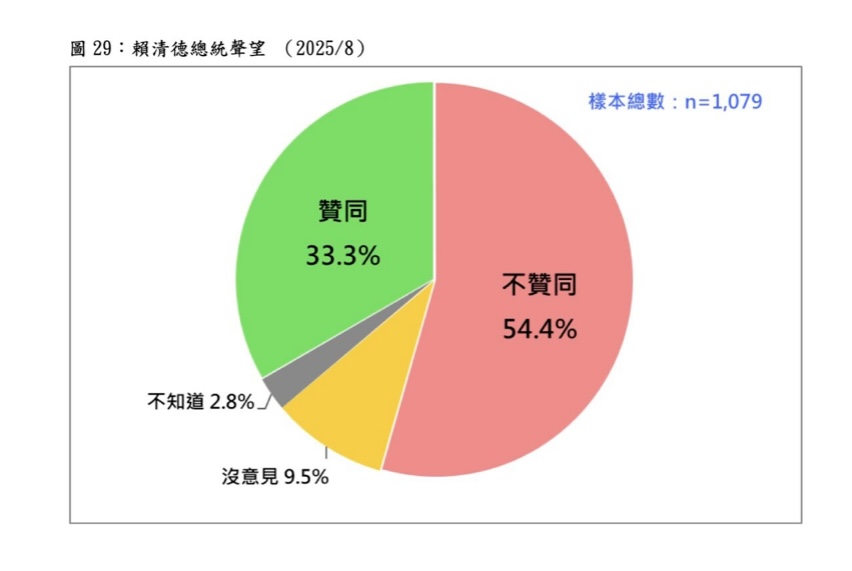照片取自行政院人權資訊網
【聚傳媒奔騰思潮專欄】筆者日前受邀參加《反歧視法》草案研討會;行政院於2024年5月初公布的《反歧視法》草案所引起之社會震盪,遠未平息;若干問題所涉之基本邏輯與價值取向爭議,值得進一步釐清。「歧視」這個詞實際上是一種價值判斷,而價值之形成,往往非一朝一夕之功。例如:在一般情況下,沒有人會歧視見義勇為者,沒有人會歧視一個正在上學途中的學生,也沒有人會歧視一個正在吃冰淇淋的小朋友。換言之,當「歧視」發生時,必然是一方對另一方的某種狀態或行為進行了價值判斷,內心給予較低評價,進而表現於外,甚且給予差別待遇。
歧視者與被歧視者之間通常未見得會有價值取向衝突,例如:某甲之行為構成犯罪,某乙因而鄙視某甲,某甲即便心中不悅,卻也認為自己的犯罪行為並不可取。真正發生問題的是,某甲與某乙對某一狀態或事物之評價不同,而且至少其中一方感覺這種不同評價與因此導致之行為,將引發另一方不快。於此必須先澄清的是,人們往往會不假思索的認為,在這種情況下,設若甲方不接受,或不認可乙方的行為時,乙方就受到了來自甲方的歧視;實際上這是一種完全錯誤的推理。我們可以將上述情況例示為,甲方不接受,且不認可乙方之公然猥褻,但乙方認為這是個人自由,當甲方因此鄙視乙方時,乙方指責甲方以言行對其歧視,並通過某部法律限制甲方將其認可之價值取向表露於外;亦即,甲方有義務容忍乙方表現出其所認定之不合宜行為,而且必須限制自己之言論自由,以避免冒犯乙方。
於此之問題在於,何以甲方不認同乙方之行為時,甲方就必須三緘其口;而乙方卻可以不必顧慮其行為是否冒犯甲方,且得以繼續為之?於此即存在一重要價值判斷,就是哪一方才是對的?對錯之標準何在?何以某標準可作為評判對錯之準繩?以及行政、立法、司法等三權,在這此類重大價值問題上之權力邊界?
從絕大多數人認可的民主憲政體制視角來看,上述問題並不難回答,因為不論是行政、立法,或是司法,其所代表的都必須是多數人的共識,當某一議題無法達成共識時,三權中的任何一權,都應當靜待社會爭議降低,待共識逐漸形成之後,才能據之提出草案,進而立法,並以之進行裁判。大法官在審理類此案件時,應提醒自己並非立法者,更非得以凌駕於民意之上的超人類;大法官是國家與民族的臉面,尤其不能自甘墮落為黨派政爭之工具;特別是要避免將大法官個人的那些說不清道不明,未經多重價值辯論與審視,且不知是否樸素之情感置於社會共識之上。
然而,檢視行政院版本的《反歧視法》草案可知,其具明顯價值預設,亦即以限制一方言論自由為代價,確保另一方之言行不但不能遭到區別待遇,甚至得因他人之不同評價,而得向他方請求損害賠償。此舉無異於一旦立法通過,即禁止人民發表與此一議題或人事物之不同意見,違者須承擔法律責任。筆者於此不僅要提出質疑,有關單位究係根據何種「正當理由」?得以此方式箝制人民之言論自由?其之謬誤,筆者可將其翻譯為白話文如下:「既然你可以不在意我的價值取向,或是說你可以直接冒犯我的感受;為什麼我就不能反對你的價值取向?或是說不能冒犯你的感受?特別是當我的價值取向,至少截至目前為止還是多數人民的共識時,何以多數就必須服從少數?如果少數才是正確的?那為什麼選總統時,不讓獲得最低票的候選人當選,而是要讓獲得最高票的人當選?」
筆者並此甘冒不同價值取向者之大不韙,提出一具體實例,敬供各界方家指正:三年前,筆者正於臺北市環河北路開車,偶然聽到一檔廣播節目,主持人正與一位女性同性戀受訪者交流,該女同性戀者與其伴侶為了擁有自己的孩子,借用他人精子,並前往東南亞進行生育,因此行為在臺灣仍屬違法。此位受訪者為確保胎兒與其同性伴侶均有基因連結,便由其中一人提供卵子,受精卵則植入另一人子宮中。然而,由於基因不匹配,懷孕一方出現嚴重排斥反應,必須頻繁就醫,服用大量藥物,以降低排斥反應,身心飽受折磨。在節目中,主持人和受訪者談及這段經歷時,均哽咽落淚,認為她們為愛情付出巨大犧牲。
然而,從胎兒的權益角度來看,這名胎兒本應在與卵子匹配的子宮中成長,卻因其母親基於愛情之考慮,而被置於不利其生長的環境中孕育。具備一定醫學常識者均知,當胚胎的基因與懷孕之母體不匹配時,免疫系統很可能將胚胎視為「外來物」,從而引發排斥反應;部分女性必須使用免疫抑制劑,或其他藥物以減少排斥反應。現代醫學雖能通過免疫調控藥物減少風險,然而懷孕期間使用之藥物是否會對胎兒造成影響,取決於藥物是否能穿過胎盤屏障,以及是否具有致畸性。某些免疫抑制劑,例如:糖皮質激素和抗排斥藥物,可能影響胎兒的免疫系統或器官發育,或是增加胎兒早產、低出生體重、結構性畸形等長期風險。
由此可知,當主持人與受訪者在討論其個人之情感偉大與健康犧牲時,卻完全忽略了胎兒當下與未來的健康程度,甚至是生命安危。做出這種選擇的人們,何以能夠將其個人情感置於他人的生命權或健康權之上?更不必說,其行為已違反臺灣法律,且有相應之法律責任。
簡言之,《反歧視法》草案之核心問題在於,該法以限制一方之言論自由為代價,保護另一方仍有重大爭議之行為不受評價,甚至賦予其損害賠償請求權。此舉不僅侵入一般人基於社會共識做出價值判斷的基本人權,更有凌駕主流民意的獨裁色彩。在民主憲政體制下,三權分力,且三權均應以多數人民之共識為基礎。我們從保障胎兒之生命權與健康權一案中可以感知,至少在華人世界範疇內之共識,人之生命健康等權利與人之愛情相衝突時,法律須優先保障人之生命與健康,而非人之情愛需求。
實際上,所有法律的基本精神都蘊含著公平訴求,當有歧視出現時,若非違法,就是該法律違反了公平原則,甚且可能違憲。換言之,當前制度本有匡正種種歧視行為之法律工具,實無必要另外制訂歧視法;因為歧視法一旦生效,等同於宣告對於不認同歧視法內容者之歧視與壓迫。其將付出之巨大社會代價,難以估量。2024年底美國大選結果,以及對覺醒運動之覺醒,即為前車之鑑。筆者相信不論是執政黨與在野黨,均能有所體會。當社會共識尚未形成時,最好的應對方式,應當是充分討論,充分反思,並靜待可能之優缺點盡可能的浮現,且參考他國之情況後,再行審慎決定不遲。
作者為法學教授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