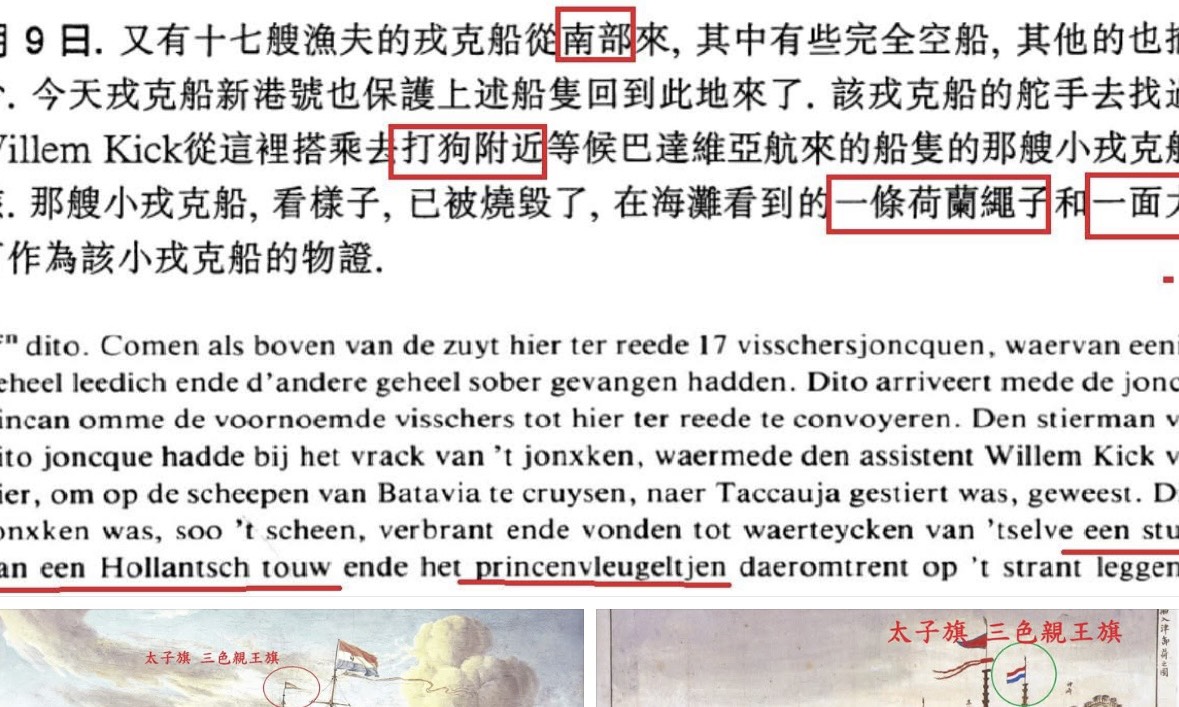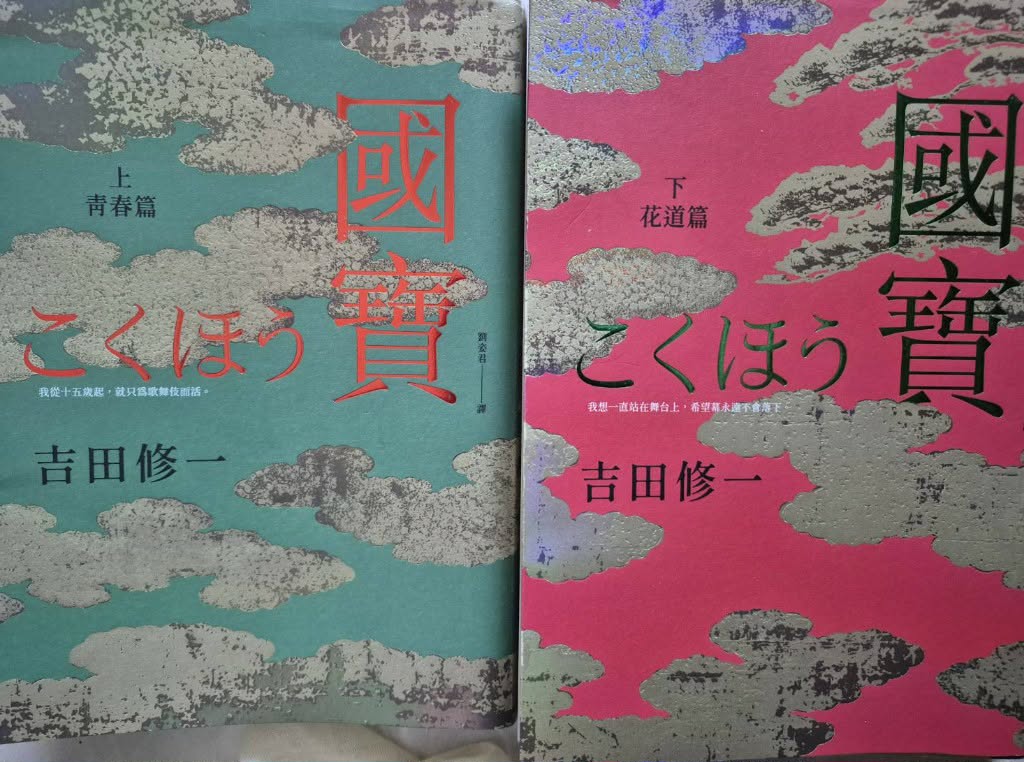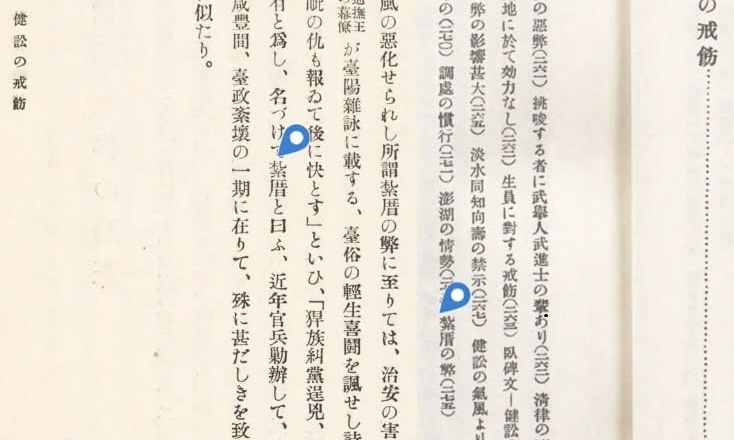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蔡詩萍專欄】都說:生死一線間。但那一線,往往並不截然。醫生雖然宣告父親去日不多,但那一條線在哪?沒人是上帝。
我回家看父親。他從醫院回來後,便安靜的睡著。呼吸均勻,面容安詳,要不是醫生已經告訴我們他必然的去向,我真的以為他是在睡午覺。
屋外陽光炙熱。氣溫高達三十四度。大弟弟撫摸父親額頭,好像有點發燒。我去鄰近藥房,買嬰兒退燒的貼布。
藥師看我選大塊的,提醒我:嬰兒不用那麼大喔!
我微笑告訴她:我老父親要用的。
她歉意的走過來,幫我選了中型的貼布,說太大的,老人家或許吃不消。
我離開藥房。對街一間規模不小的牙醫診所,陸續走出來四五位身著醫護服的年輕女孩。牙醫診所鐵門半降,應該是週末上半天班吧,幾個年輕女孩氣氛融洽的踏出診所。下班了。放假了。但誰知道每個人真正的心情呢!
日頭炙熱。我不過走了幾分鐘,額頭滿是汗珠。
父親最後的人生,我們都希望他走得平順,無憂,無慮。
有點發燒亦無須送醫了,用退熱貼布,讓他舒服就好。醫生在電話那頭,輕聲的交待我們。
我小的時候,有一次發燒,父親母親焦急帶著我,緩緩走向街上,去一家診所看病。
發燒的我,渾身虛弱,一步一步的,牽著媽媽的手。父親腳步很快,急著往前。
我其實極不想看病。發燒去看診,那年代多半會打針,打在屁股上痛死了,回家還要吃那苦得要死的藥粉,我每吃必吐。
不知是心理作用,還是夜涼如水,走著,走著,我竟然精神變好了!
我嚷著,我病好了,我病好了!父親過來,手掌貼著我額頭,對母親說:奇怪,他退燒了耶!
但我們還是去了診所,醫生說小感冒沒發燒不礙事,開了藥,沒打針。
回家的路上,我喊著肚子餓,父親母親對看一眼,帶我到市場邊上的攤子,吃了一碗陽春麵。
一碗清湯,一坨麵條,上面灑一些蔥花,一片豬肉,父親母親站在一旁說才吃過晚餐不餓,我滿頭大汗,連麵帶湯全吞下肚。
那是我少數記得的,小時候的日常生活。也許細節有出入,也許時間點不確定了,但發燒,上街,看病,吃麵,牽父親母親的手回家的畫面,卻很清晰。
父親母親都不記得了。小孩生病是日常,小痛小病,他們記不住很合理。但對我,發燒很神奇的走著走著自己退了,那碗難得的陽春麵湯頭甜美,蔥花香氣襲人,一輩子難忘。我記憶基因裡對陽春麵,特別是上面鋪一片豬肉的美好,終身難忘。
我突然流淚了。在炎炎的日頭下,在從藥房走回家的路上。如今我父親發燒,我們卻束手無策了!只能買一盒嬰孩退燒貼回去。
我可以帶著他,上街,吃一碗陽春麵,然後他精神奕奕告訴我:「哦沒事了,沒事了,我們回家吧!」嗎?
我站在街頭,忍不住眼淚。
進門前,我抹抹眼眶。弟弟走出來看著我。我聳聳肩,沒吭聲,把退燒貼遞給他。
我說想在外面透透氣。他點頭,返身,闔上門。
我聽見他在裡面:老爸,大哥買退燒貼回來啦,您乖乖躺著,我幫您貼上,一貼就舒服啦!來,乖。
我站在門外,深呼吸,長吐氣。深呼吸,長吐氣。心情的波浪慢慢緩下來。
我們家住進這棟房子也超過三十多年了。從眷村遷出來,這房子是父親懸念所及的夢想:每個孩子都要有自己的房間,不管是不是很小。
不管房間是不是很小,父親心念所在:都是這個家,都是他的孩子。
如今,他要在這棟房子裡,安詳的躺著,安詳的入夢了。
我什麼都不能做。我只能去藥房替他買一盒嬰兒退燒貼。
我只能記得,我只能想念,記不真切哪一年的哪一個夜裡,我發燒了,我牽著父親母親的手出門看診了,路上晚風習習,我退燒了,我吃了一碗熱騰騰陽春麵,街燈明亮,迴舞著飛蛾,那時父親很年輕,母親更年輕,那是我們家胼手胝足的一段里程碑,我當時很天真,不懂世間有一種「我不餓」,是「做父親母親的不餓」;後來當然漸漸懂了,但父親卻老了,而如今,父親卻要離開了!
作者為知名作家、台北市文化局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