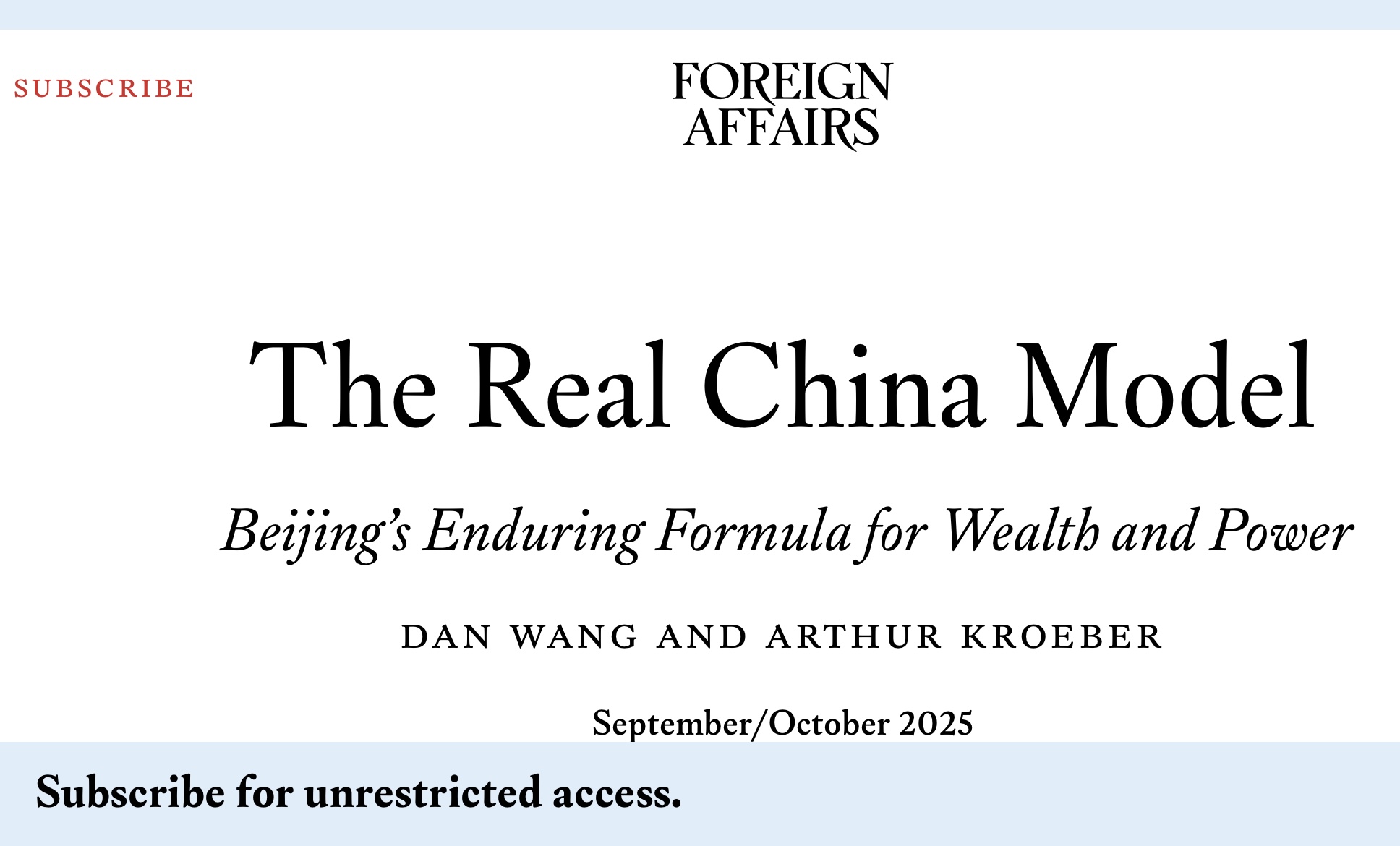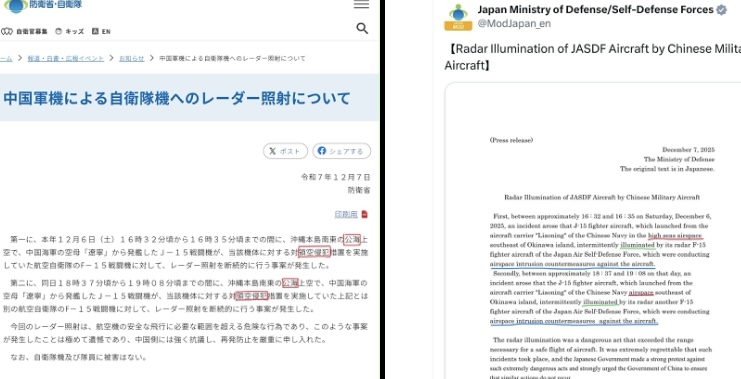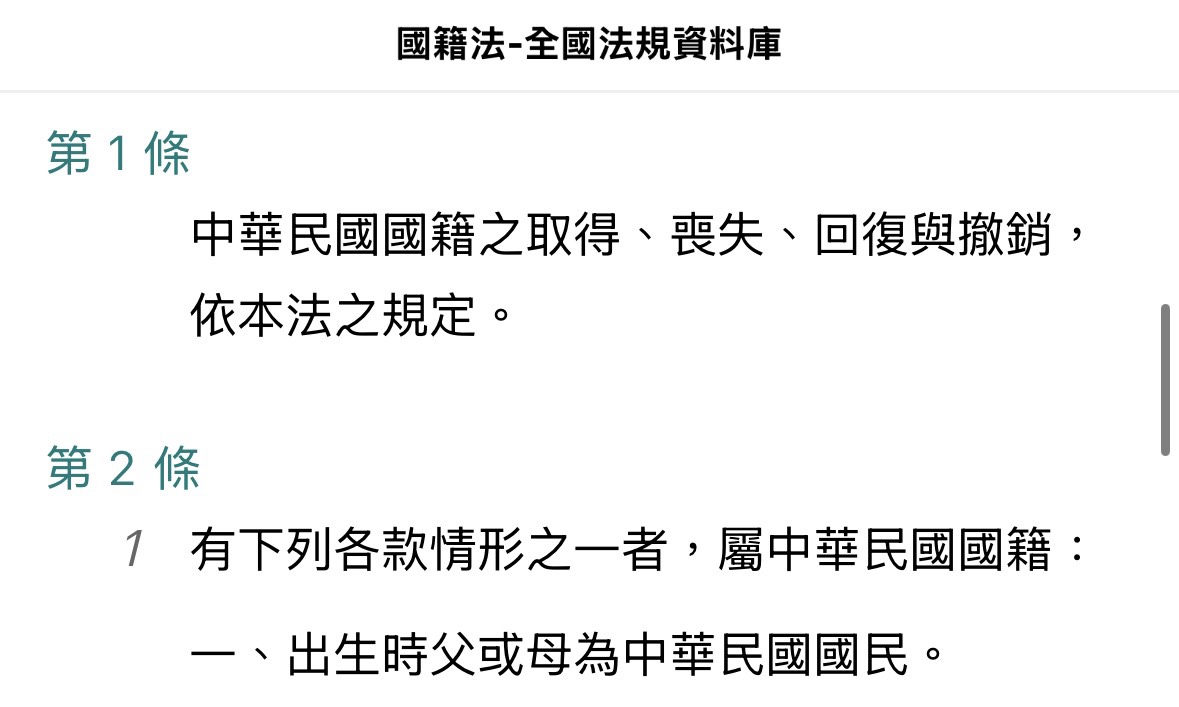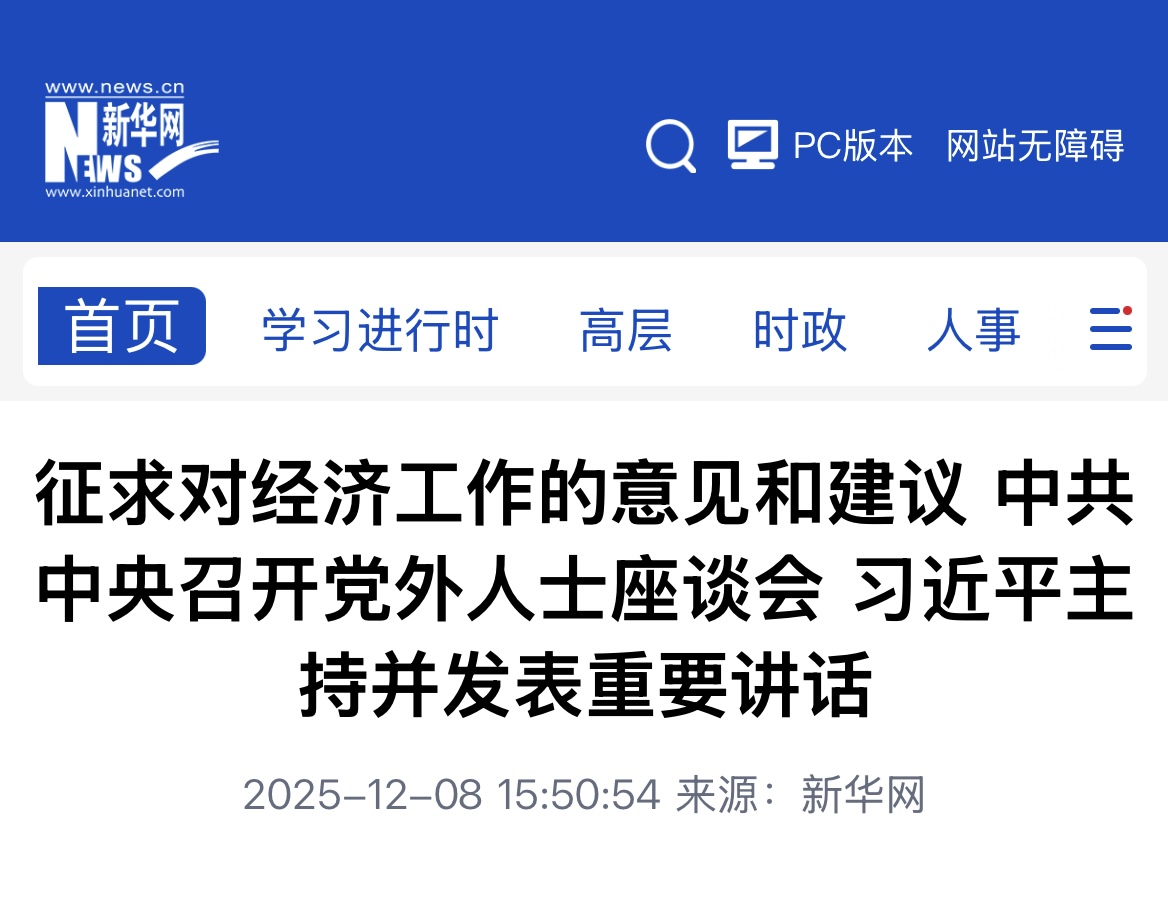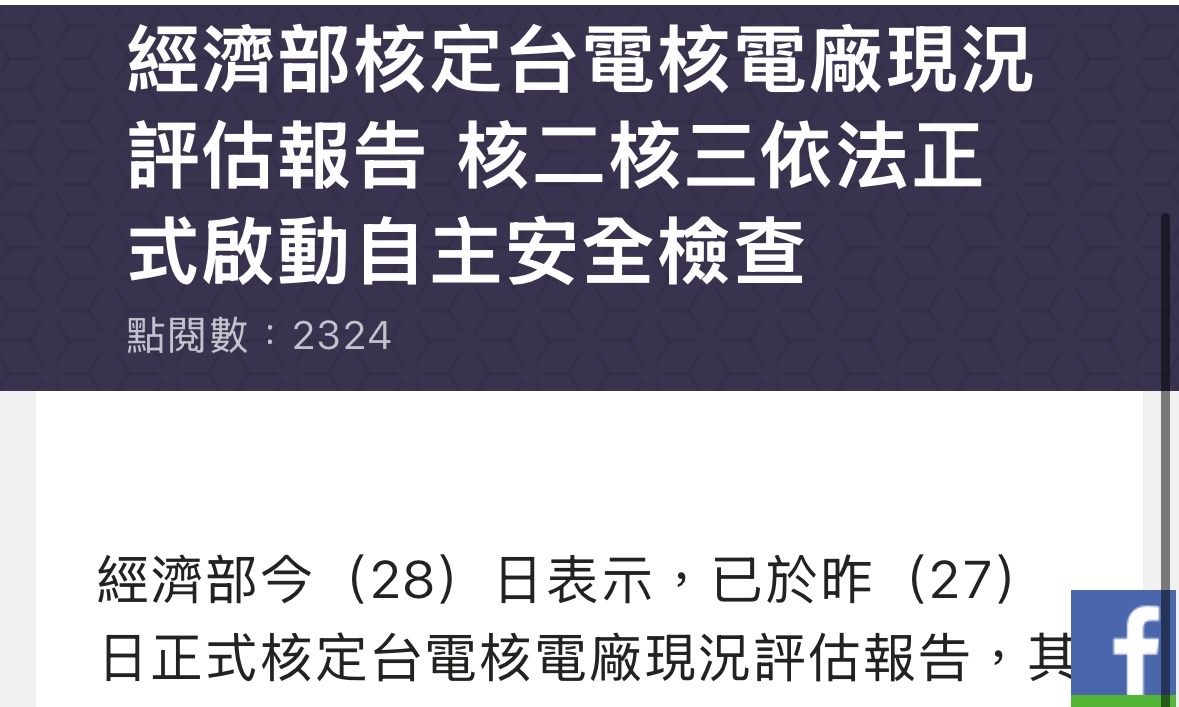照片為《外交事務》官網截圖
【聚傳媒上官亂文章】在不少美國鷹派、台灣綠營政客和評論員眼裏,如今的中國經濟不僅停滯,而且還停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廉價、山寨、土地財政。大家至今習慣性地用「中國經濟要崩潰了」「房地產泡沫要崩了」「中國只會山寨」來安慰自己,好像只要不斷重復這些陳詞濫調,中國就會自動停下腳步。如果誰提出質疑,則立馬被打入「中共同路人」的陣營。
可現實並非如此。前兩月,《外交事務》發表以《真實的中國模式》為題的文章,直言:「中國模式之所以奏效,是因為它在許多方面做對了,為中國企業家創造了成功的條件。」 這句話幾乎擊中了美國和台灣鷹派不願面對的痛點:中國早已不再是那個依賴低成本勞動力和房地產紅利的國家,中國模式也早已改變。雖然GDP增速減緩,但中國的戰略重點也轉移了:它正在主動換擋,從追求速度轉向追求韌性和自主性。
中國模式的真正秘密:早已不再大「撒幣」
《外交事務》首先提到: 大家喜歡說「中國產業靠補貼」,除了一語否定中國的產業補貼政策,還有一個潛台詞:只要政府掏錢,任何國家都能復製中國的成就。
但如果補貼就是全部邏輯,為什麽幾十年來美國政府也投了數千億美元,卻遲遲沒能在新能源車、光伏甚至電池領域形成完整的生態?台灣也補貼裕隆十幾年,結果呢?
答案在於,中國模式的真正秘密不是「撒錢」,而是 「基礎設施 + 產業生態」。基礎設施以中國電網為例,規模世界第一,不僅覆蓋廣,還能以極低的價格為產業提供穩定電力。這是為什麽中國的AI大模型公司可以瘋狂訓練,最終找到賽道,而美國公司卻要計算電費賬單。
其次,中國有完整的產業鏈,從上遊原材料到下遊裝配廠幾乎都能在國內或鄰近地區找到配套。造一台新能源車,90%的零部件都可以在中國幾百公裏的範圍內完成。
高鐵、港口、公路在客運量的回報上大多數處於虧損狀態,但另一方面,卻讓貨物在國內快速流動,大量工廠長期積累下來的生產經驗,使得新產品可以快速量產、快速叠代。這些都是生態鏈的另一面。
《外交事務》這樣概括這種優勢:「中國的製造能力和知識積累,源自多層次的基礎設施投資和對生態系統的理解,而不是單純的資金補貼。」
這些條件疊加起來,讓中國企業不僅能造出產品,還能「卷」出規模優勢。比亞迪能在一年內把電動車價格拉到其他國家無法企及的程度,這不是補貼能單獨解釋的,而是整個生態協同的結果。所以,當「中國崩潰論」的政客和名嘴們還在說「中國沒有創新,只會偷」,他們實際上錯過了最關鍵的事實:中國已經在打造一個別人很難模仿的系統性優勢——即便這個優勢是「一將功成萬骨枯」的卷王模式。
中國新模式的困境與挑戰——尚可以解決的副作用
當然,中國模式並非沒有問題。
首先是補貼的副作用。大量資金流向製造業,帶來了腐敗與低效。以半導體行業為例,自2014年以來,中國在芯片產業投入了超過1000億美元,但其中不少項目要麽爛尾,要麽成為騙補騙局。清華紫光的破產、國家大基金多位高層落馬,都是鮮明的例子。
其次是 產業內卷。補貼讓許多本來該淘汰的企業活了下來,導致過度競爭。太陽能、智能手機、電動車等行業,企業為了搶市場份額不斷降價,結果大家利潤都極低,留給研發和創新的資金反而有限。
第三是 結構失衡。製造業受政策扶持,但服務業被嚴格監管。金融、教育、醫療等領域幾乎被腰斬。這讓就業增長嚴重依賴服務業的中國陷入困境——就業不足、工資停滯、消費疲軟。
再加上房地產下行,居民資產縮水,消費信心更低。於是,中國經濟增速下滑,通縮壓力頻頻出現,想實現年均5%的增長都變得不容易。
同時,中國製造業過剩的產能越來越依賴出口。這雖然顯示出產業競爭力,卻也意味著中國越來越可能遭遇更多國家的保護主義,最為顯著的就是鏖戰數年的中美貿易戰。
但是正如《外交事務》提醒的那樣:「中國的補貼確實造成了浪費和過剩,但這只是贏得未來行業領導地位的副作用。」 換句話說,這些問題並非微不足道,但認為它們足以阻礙中國的技術發展勢頭則是一個嚴重的錯誤。現在的美台應派最大的問題,就在於過度放大了這種副作用,而輕視中國模式的真正優勢以及中國解決這些問題的能力。
互聯網在其發展初期,人們普遍認為它能夠打破政權對信息的壟斷,並使普通民眾更容易在遠距離組織起來。但現在,中國建立了一個龐大的國內互聯網,迅速連接了幾乎所有人口,造就了字節跳動、阿裏巴巴和騰訊等世界級的巨頭,最終走了出去,並且成為撬動中美關係的槓桿之一。《外交事務》認為,這得益於北京早期大力推廣手機,中國企業幫助開創了移動互聯網。換句話說,這仍然是 「基礎設施 + 產業生態」的結果。而自稱言論自由的美國、台灣當局,則正在「民主」、「國安」的口號之下狂奔上言論管製之路。
應對之道:戰略重點轉移
更重要的是,面對以上挑戰,中國並沒有坐以待斃,而是做出了一些明顯調整。
主動「卷」,產業洗牌。電動車行業就是例子,過去幾年企業數量從57家降到49家,市場集中度提高,頭部企業比亞迪、小鵬、理想等更具競爭力。
減少補貼。中國政府開始認識到「撒錢」的邊界,逐步取消對低效企業的支持,讓市場機製發揮更大作用。
戰略重點轉移。這是其中最值得註意的,就是北京已經告別唯GDP的時代。中國這幾年設定目標不再是「高速增長」,而是 自給自足與技術突破。北京已將實現技術霸權作為首要政治優先事項。它用於推動技術進步的補貼造成了大量浪費,但這是在未來行業取得領導地位的副作用。這一點,在近幾個月的華爾街日報中也有體現,雖然六七月分的PMI有所下降,但是很多時候是地方政府對於電動車等行業生產的主動降溫。這當然首先是為了避免產業過剩,但同時意味著,GDP已經不再是地方政府發展唯一的考量。
所以,《外交事務》該文認為,中國經濟雖然承壓,但並非外界所說的「要崩潰」。相反,它正在主動換擋,從追求速度轉向追求韌性和自主性。
美台鷹派的手段與誤判
在新的中國模式面前,美國鷹派、反接觸派、台灣綠營的反應主要是 遏製與打壓,以及隔絕接觸與汙名化。
川普政府推出芯片出口管製,拜登政府繼續並加碼,限製中國獲取高端AI芯片和半導體設備。與此同時,美國通過《芯片法案》《通脹削減法案》投入數千億美元補貼,希望重振製造業。然而,效果卻很有限。華為在製裁後不僅挺過來,還在芯片設計上取得突破,手機重新殺回市場。中芯國際在被封鎖後依然實現了7nm工藝量產,遠超外界預期DeepSeek等中國AI公司,憑借廉價電力、海量數據和人才,在大模型上只比美國落後半年左右。
正如文章所說:「美國正在派律師參與一場工程糾紛。」 這句諷刺意味極強,點出了美國依靠法律和管製,而不是工業和工程的現實。
更糟糕的是,美國自己的產業政策往往虎頭蛇尾:數十億美元的電動車充電樁項目進展緩慢,全國網絡至今沒建成。輸電系統擴張受製於繁瑣審批,新能源潛力無法釋放。製造業產出仍低於2008年金融危機前水平,連軍工產能都不足以滿足烏克蘭戰場需求。這讓美國的戰略處境更加尷尬:一方面限製中國收效甚微,另一方面自身工業基礎持續衰退。
美國當然還有獨特的優勢,在軟件、生物科技、AI算法領域仍然領先;頂尖大學和科研體系仍是創新源泉。可惜,這些優勢正在被自身政策消耗。川普第二任期中,科研經費被削減,大學因政治鬥爭受到幹預,移民限製讓高端人才流向其他國家。
於是,《外交事務》就警告說:「如果美國政策製定者繼續低估挑戰,那麽在能源、工業品乃至人工智能領域,美國及其盟友將被迫承受去工業化的壓力。」這意味著,美國在對抗中國時,可能在自己最強的領域失去領先。
美國應該與中國競爭,以保持其整體技術領先地位,並維持實現廣泛繁榮和國家安全所需的產業。但美國政策製定者必須認識到,他們目前的策略——出口管製、關稅和漫無目的的產業政策——是無效的。僅僅試圖減緩中國的發展是行不通的。
台灣也同樣應該認識到,隔絕、歪曲一個真實的中國大陸,並不能實現自保,抹紅在野黨也無法實現成功大罷免,汙名化陸配也無法轉移內政的積弊。只有面對對岸的現實,承認自身的問題,才能找到未來的鑰匙。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投稿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