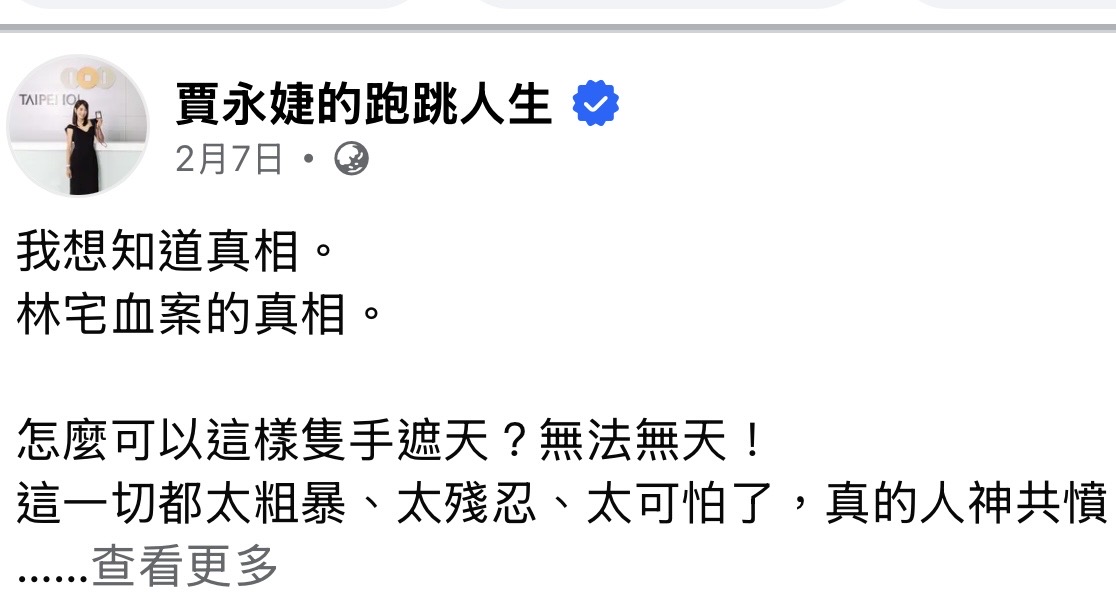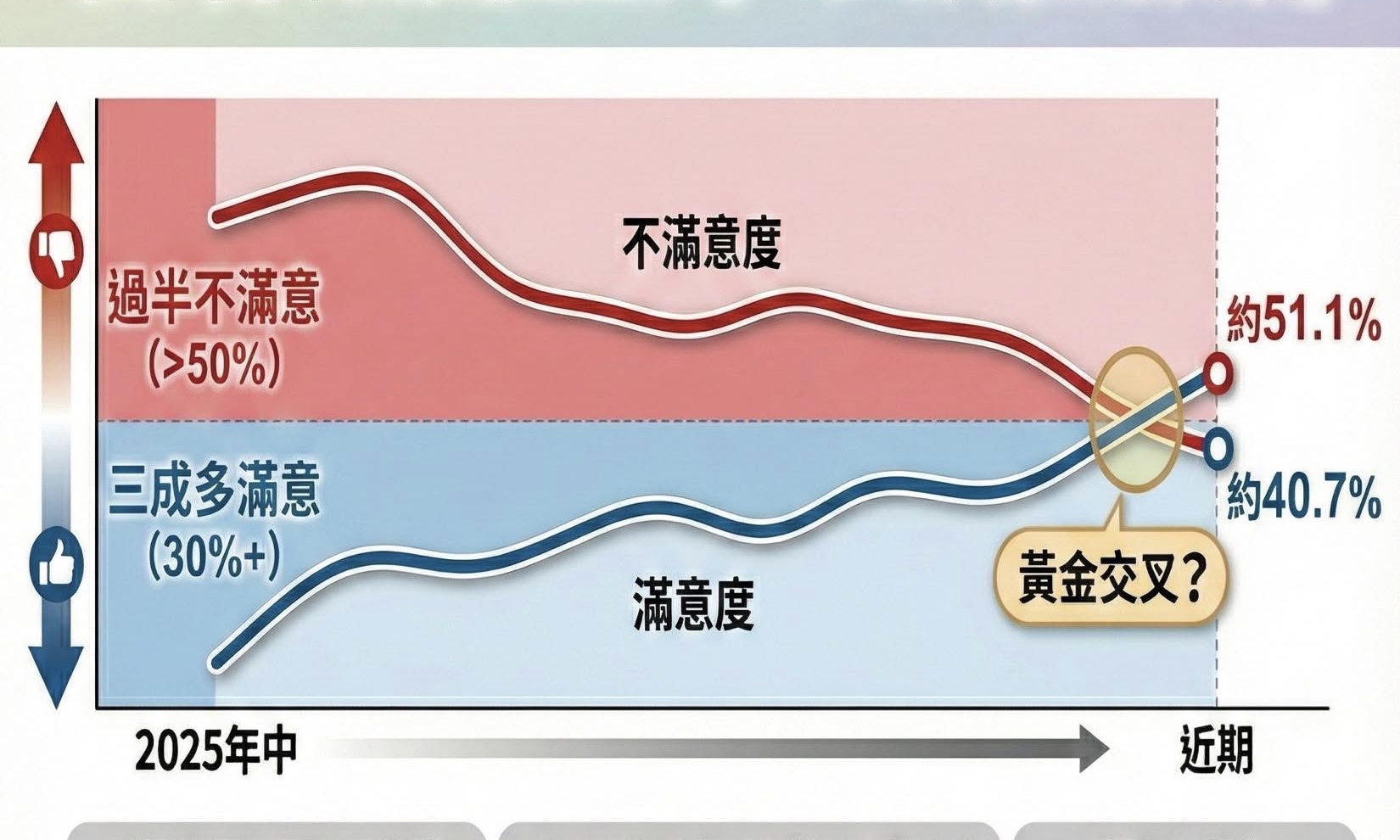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上官亂文章】近來,中國大陸諜戰題材戲劇「沉默的榮耀」熱播,主題是台灣1950年的「第一匪諜」案吳石案,沒想到,在海峽對岸的台北,竟也帶動了馬場町紀念公園(槍斃吳石之刑場)的市民和遊客獻花現象。據媒體報導,陸委會表示已前往觀察,認定花束署名卡片多為陸籍人士,目前沒有看到來自台灣人的獻花。他們認為由於不少陸籍人士可以用商務交流等名義來到台灣,或許也是藉由這個機會到馬場町紀念公園打卡、獻花。
根據移民署前不久公布的數據。今年前9個月,大陸地區人民進入台灣地區的數量達46萬7,456人次,除去小三通遊金馬的15萬,商務交流5萬3,779人次、專業交流1萬829人次,剩下近30萬人來到台灣本島的陸籍人士是通過第三地來台觀光的,平均每天大概有數百位陸籍遊客來台。所以獻花的都是這些觀光客,而沒有台灣人嗎?於是10月24日,我來到了現場,發現了出人意料的真相。
當天儘管陰雨綿綿,但是遠遠就能看到馬場町紀念丘前確實鋪滿花束,除此之外還有鳳梨酥、金門高粱等祭品。其中有一小部分花束的確附帶著簡體字的卡片,寄託對「烈士」的哀思,直言向吳石致敬。但是獻花者並非都來自觀光的第三地大陸客。在那裏停留的十幾分鐘里,我遇到了三波獻花者。
第一波是一位澳門青年和一位台灣女士,他們帶著關於台灣族群政治的研究文獻,談論著對中華民國的認同感,為紀念丘獻上了鮮花,並倒上高粱酒。他們說,他們每年都會來獻花,今天已經有四波台灣同仁過來獻花了。
第二波,是一位台灣年輕女士,攜帶著一大堆花束。她說,很多大陸人在抖音上討論「沈默的榮耀」,她也參與討論,於是很多大陸網友委託她幫忙獻花,以表達對吳石等人的哀思,這已經是她第三次過來了。言語間,她正將一束花、一瓶酒、一張來自四川綿陽網友的卡片放在紀念碑前。原來,有一些簡體字的卡片是這樣來的。
第三波獻花者,是幾位穿著「統一義勇軍」馬甲的幾位阿伯。他們似乎常上新聞,是比較活躍的統派群體。
至少這三波人裡,沒有一位是大陸觀光客。
有趣的是,民視新聞對這些獻花者有過報導,文中直言:「小粉紅來台灣,不先去景點觀光,而是先到馬場町公園,朝聖"紅色景點」。
可是,馬場町並不是什麼紅色景點,而是是陳水扁時期就認定的「白色恐怖」遺址,1998年,时任台北市長陳水扁決定在馬場町、六張犁設立「白色恐怖紀念公園」,以紀念白色恐怖時代犧牲之政治犯。更是2016年蔡英文執政後,被文化部認定的白色恐怖不義遺址。現在卻被媒體描述成紅色景點,實在諷刺。
另外,陸委會發言人還提到,「《沉默的榮耀》在對岸引起一些討論,不過台灣沒有聽過有人討論,對於台灣來說,這是翻過去的一頁,對岸把這個事情拿出來重新炒作,把這些人當做英雄,其實對於台灣人來說較無感。」
「這些人」是誰?吳石?還是馬場町的犧牲者?這些事情真的翻篇了嗎?
在民進黨的敘事里,馬場町是一種國民黨威權主義的象徵,他們的存在,既有人權價值、轉型正義的表達,也在為本土派的「受害者敘事」服務。既然還要為民進黨的本土化敘事服務,那麼馬場町就不會是「翻過去的一頁」,哪怕對民進黨來說也是如此。更何況,吳石的家屬,前幾年也得到過政府的補償。
當時吳石等人被槍斃後,整個案子牽連者甚眾,包括吳鶴予、方克華、黃德美、吳石的妻子王碧奎之家屬、江愛訓等人。2013年,《戒严时期不当叛乱暨匪谍审判案件补偿基金会》依據《戒嚴時期不當叛亂暨匪諜審判案件補償條例》,補償受牽連之吳鶴予等人合計690萬元,其中受補償之人就有吳石之妻王碧奎之家屬。直到2019年,監察院還通過受昔日吳石牽連之「冤案」調查報告。為諸多受牽連者平凡。這件事情,並沒有翻篇。
其實,在早已民主轉型的台灣,這種『彼之「匪諜」,我之「轉型正義」,他之「烈士」』的魔幻現實,不止上演一次。終極問題在於,台灣的執政黨一再地迴避,或者放棄跟大陸相關的歷史敘事。以二二八的敘事為例。
學者黃種祥在《二二八事件真相辨證》一著中寫道:對於二二八事件的論述,國民政府在事後陸續發表幾篇解釋及推卸責任的文章後,緘口不談,反而使事件的詮釋權落在其他人手中;中共在政治考量之下,大量製造相關論迹,成為現今史料的主要來源之一。
學者尹章義認為,緝菸事件引爆了民眾久蓄的不滿,形成蔓延全島的抗爭,這段時期全臺灣陷人無政府狀態,島內一部份人有獨立的傾向,一部份人士亟望回歸日本統治,少部分臺共份子附和,加上退伍的臺灣青年,造成動亂。軍隊鎮壓之後,暴動消失,但臺灣社會的許多菁英份子在鎮壓中受到摧殘,在臺人心中留下難以平復的傷痕,政府則刻意淡化事件,視為禁忌,並將錯誤的責任推給中共,中共也樂於認定就是他們策動臺灣人民「起義」。
當時能找到的相關資料,包含當事人的證言,幾乎集中在中國大陸。畢竟二二八事件之後,臺灣很快戒嚴,眾人緘口不談此事。而不少當事人逃奔對岸,後來多加入「臺灣民主自治同盟」,反而暢所欲言。
比如《大明報》的編輯陳季子、文野、薛慕等人都逃亡到臺灣旅滬同鄉會,撰寫二二八經歷,交由中共宣傳部的田漢等人發表,作為攻擊國民黨之用。而逃到香港的楊克煌、蘇新等人,也借用臺共前輩莊嘉農、林木順之名,分別撰寫《憤怒的臺灣》與《臺灣二月革命》,一方面攻擊國民政府,另一方面悄悄奪取了二二八事件詮釋的主導權。最初中共將二二八定位為「反抗國民黨的民主自治運動」:二二八事件之性質是臺灣人民反抗國民黨統治的民主自治運動,不是臺灣人民的獨立運動。
這和現在民進黨卻急於擺脫與大陸歷史的聯繫,而中國官方順勢將光復節納入中國歷史正統,有異曲同工之妙。
或許,真正值得追問的,不是「誰在馬場町獻花」,而是「誰有權詮釋這些花的意義」。在一個早已民主化、卻仍被歷史邊界劃分的台灣,記憶往往成為政治的工具——人權成為儀式,烈士成為立場,連哀悼都必須先被檢查國籍。馬場町的花束因此成為一面鏡子:它照見的不僅是兩岸之間記憶的斷裂,也反射出台灣內部敘事的困境。當一個社會無法誠實地面對與他者交纏的歷史,只能在意識形態的坐標中選擇遺忘,那麼「轉型正義」也將失去方向。那些花,不只是獻給吳石或白色恐怖的亡靈,它們更像是獻給一個被撕裂的共同記憶——提醒我們,歷史從未真正翻篇,只是等待被重新閱讀。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投稿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