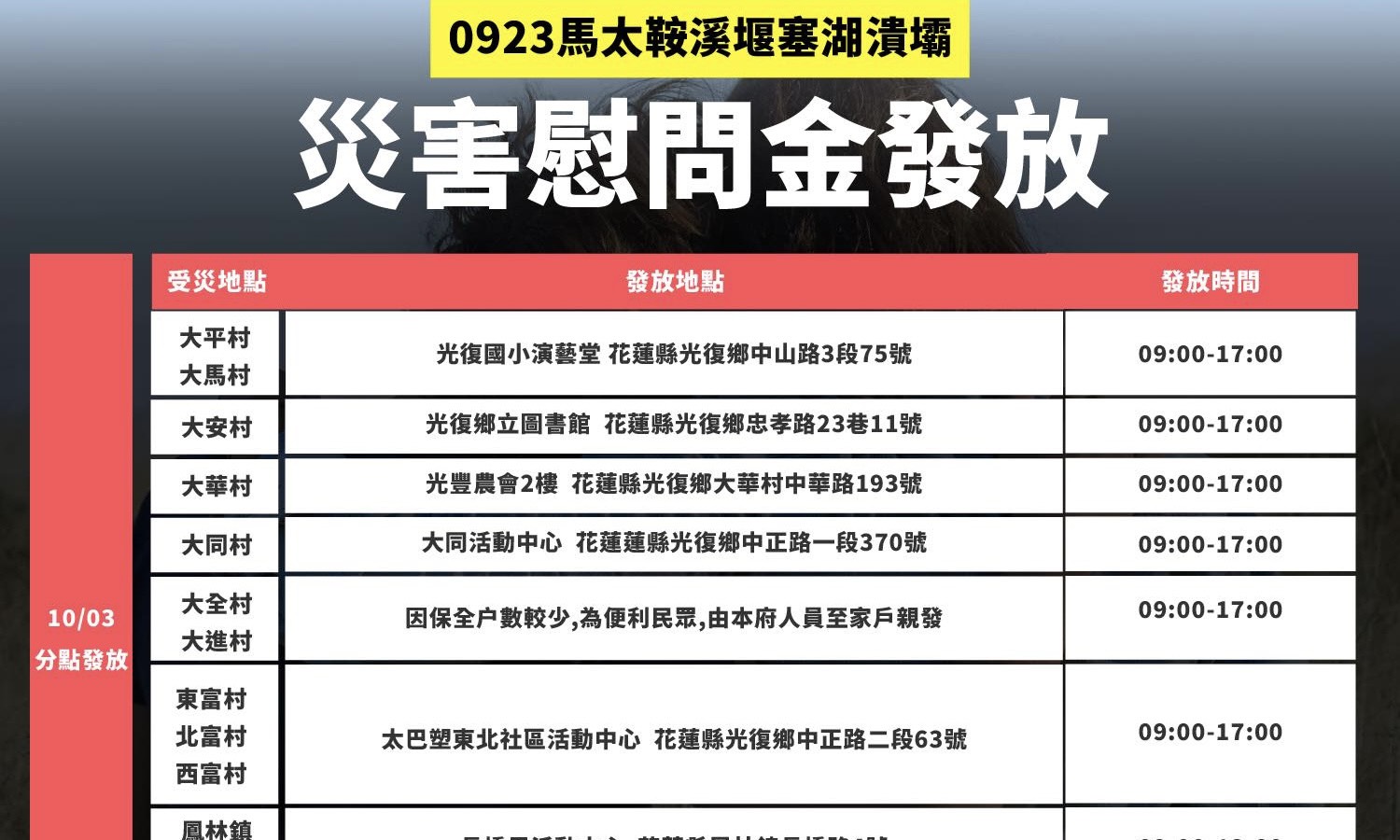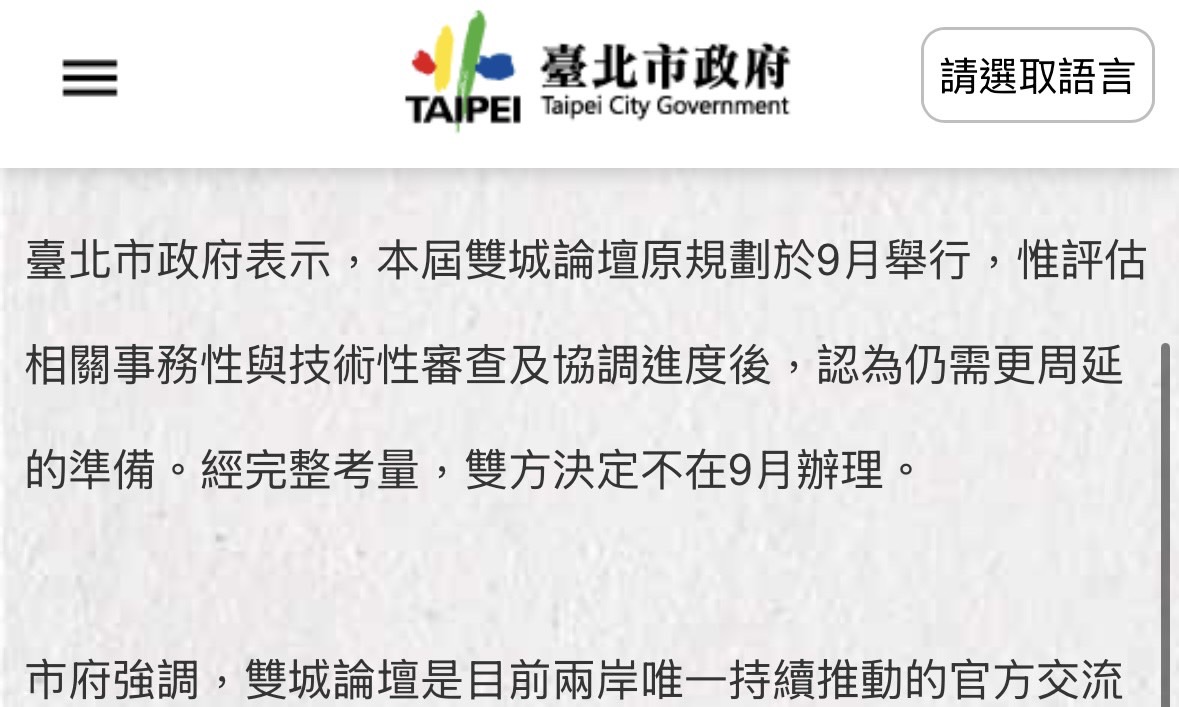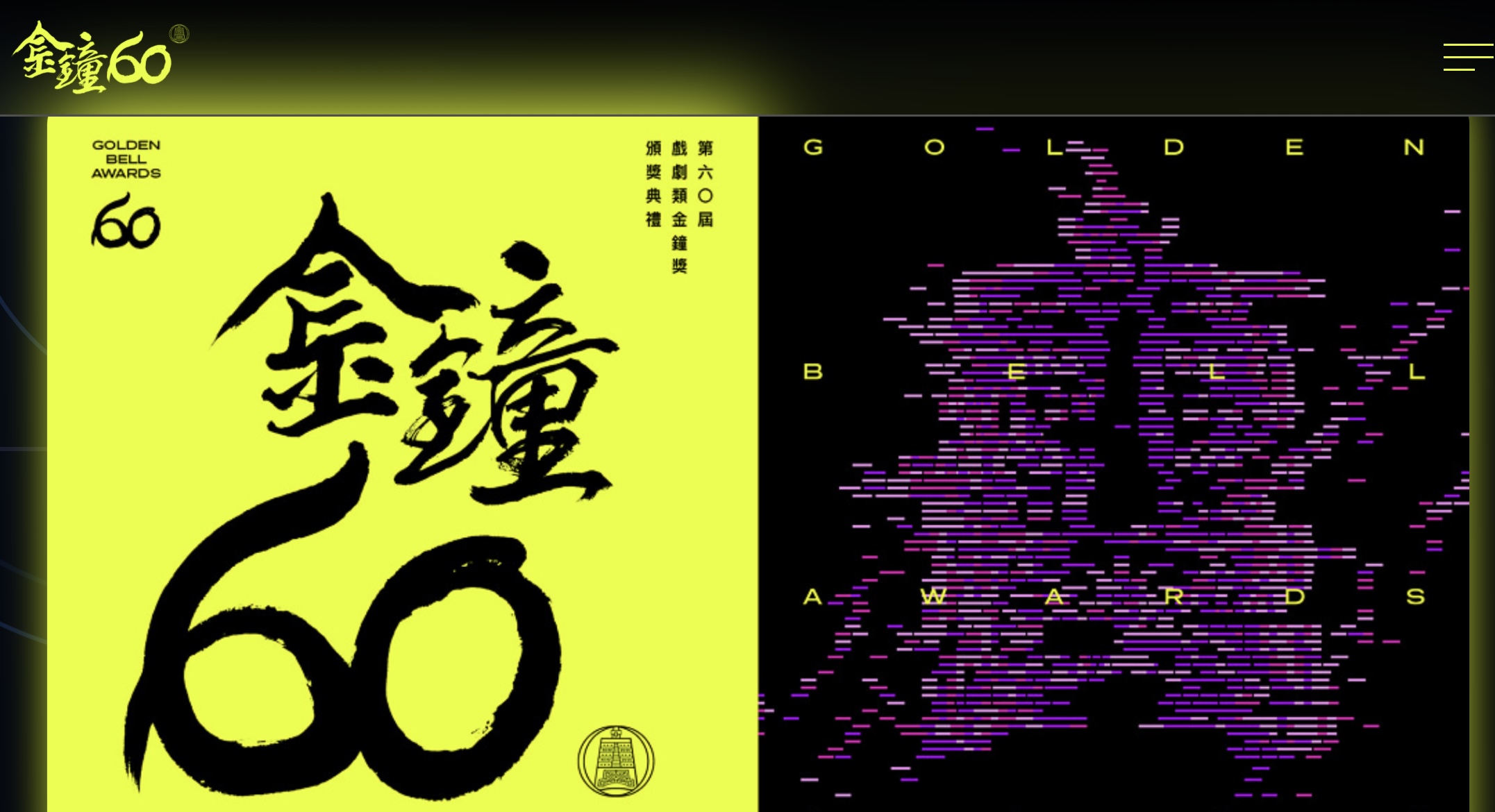照片取自總統府官方網站
【聚傳媒奔騰思潮專欄】近年來,不分光譜、立場,許多人都能明顯感受到「言論自由」在臺灣正成為一個亟需討論的公共課題。究竟言論自由該不該有邊界?又或者能否無限上綱?前陣子爭議性極高的北一女教師區桂芝事件,因其自稱「中國人」而被校方與教育局約談,引發社會譁然。同樣地,桃園亦有國小校長因在TikTok發表「我愛你中國」言論而遭調查,也再度點燃輿論戰火。除此之外,近日多所大學出現「罷藍」團體進校園擺攤募集罷免連署,學生們自述在校園裡「不受待見、受到輿論打壓」,甚至傳出文宣被毀壞、校方過度「關切」,凸顯校園言論與政治參與的張力。凡此種種,都使我們重新思考:與其只談抽象的「言論自由」,臺灣更該正視的是基於國族認同與意識形態所形成的「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在筆者與多數學界對言論自由的理解中,「言論免於被批評」並不在保障範圍內。行為人自須為言行負責;因此,公眾對「討厭的言論」提出批判,本無違言論自由的定義。然而,當批評升高為動員式的圍剿、抵制乃至於讓發言者遭受官方的行政懲處,就不僅是「反駁」或「監督」的問題,而可能落入取消文化的範疇。
取消文化一詞源於西方社群媒體,原本指網友集體抵制性騷擾、種族歧視等不當言行;如今被廣泛延伸為任何透過網路輿論將對象「消失」的行動。國家往往無須出面,輿論已先扮演「法庭」。一旦某種立場被貼上「危害公共利益」標籤,群眾便自動將批判與排除視為守護社會正義的必要代價。當標籤對準「中國認同」時,案例尤為顯著,區桂芝被匿名檢舉、國小校長遭教育局調查,莫不符合「媒體輿論先行審判,再由公權力介入」的三段式劇本。
對此現象,批判中國認同者及部分執政黨政治人物經常未完整聽取對方論述脈絡,亦忽視臺灣歷史的多元複雜,逕自將「臺灣認同」化為唯一正確答案,並將「中國」與「中共」混為一談,以此鞏固己方政治敘事。固然,住在這片土地上的每個人都可對「臺灣」賦予不同意涵:它可以是國家、地方,也可以是生活共同體,未必侷限於「國號」。若僅因為論及「中華民國在法理上仍為中國政權」便被簡化為「中共同路人」,乃至被集體噤聲,這不僅無助於民主社會的多元對話,反而加深了內部分裂,為真正的外部滲透留下縫隙。
言論自由需要界線,但更需要程序與比例原則。批評可以尖銳,但不該變為動輒毀滅的「出征」;行政機關可依法調查,卻不該倚賴輿論風向作為懲處依據。當校園裡的罷藍攤位因「政治中立」之名被關切;當教師與校長因身分認同而被追究,我們已不只是在討論言論邊界,而是在面對一場以「整體利益」甚至「部分人的利益」為包裝的新型態群眾監控。真正值得警惕的,或許不是誰喊了「愛中國」、誰擺了罷免攤位,而是全民是否習慣於用「取消文化」的方式,消除與自己價值觀不一致的聲音。
民主並非只有單一意見,而是該允許多元思想的存在。臺灣若真要強化民主韌性,第一步正是警覺「取消文化」的蔓延,拒絕用「群眾審判」替代公開辯論與法治程序,不同立場的言論即使刺耳,但仍有發聲與被理性檢驗的空間。
作者為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學生,臺北市青年諮詢委員會委員、第24屆政大學生會會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