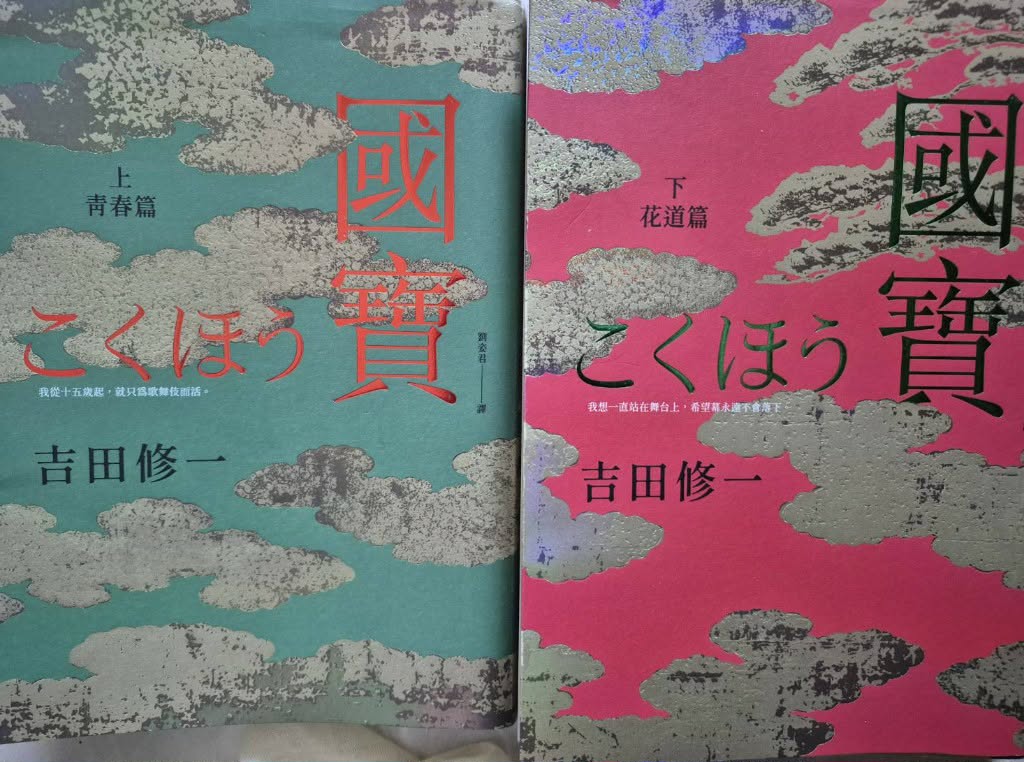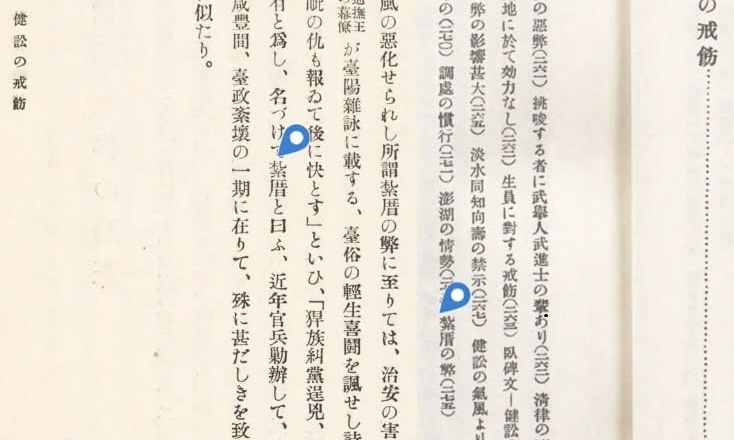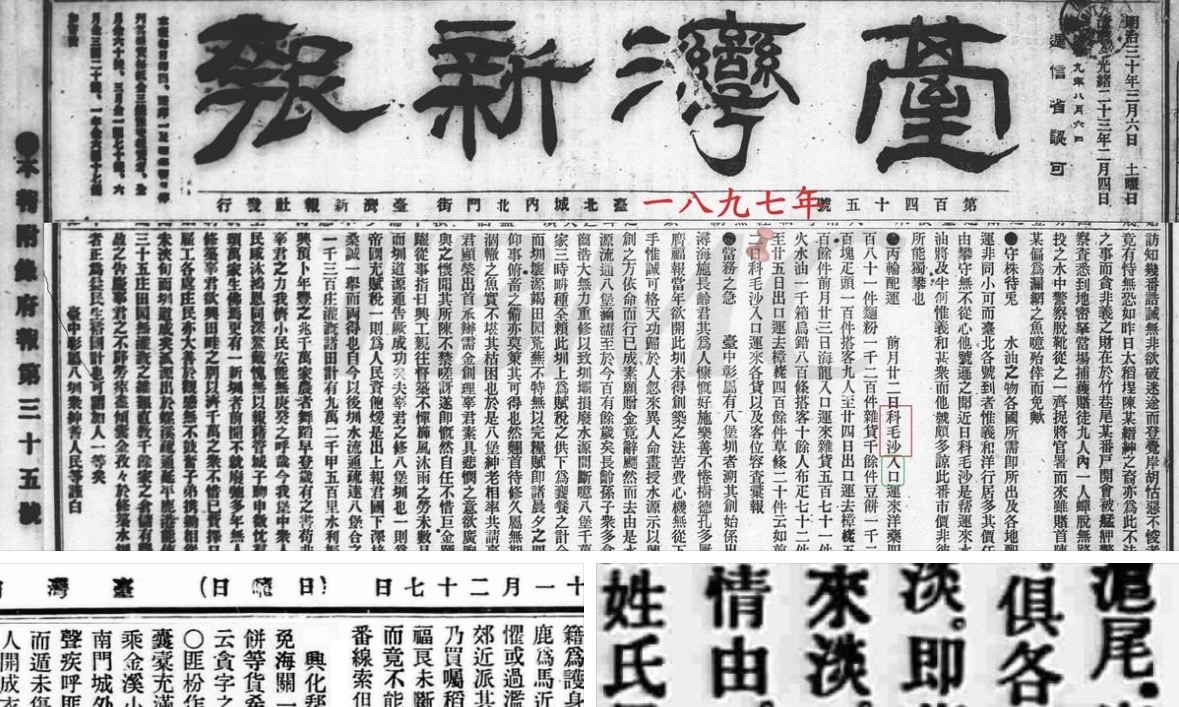照片為作者拍攝
【黃愛真閱讀專欄】騎著腳踏車,將日語交換學習的傳單貼在師大語言中心電梯旁的牆壁上,筆者和同為日本狂的同學,因此輪流接待過不少來自日本的年輕朋友,做語言交換學習。
這些來自日本東大、沖繩、關西區域的日本朋友,成為我們大三、大四,星期六、日的約會對象。也教會了我們對日本政治經濟的關注,或者池坊花道……。
小說《國寶》(新經典出版)的閱讀,再次喚醒了筆者心中的日本文化魂。「國寶」在書中的說明是「重要無形文化財及保存」,而這位文化財歌舞妓立花喜久雄的養成與成為日本文化財的過程,實在讓人非常好奇。《國寶》上冊講述立花喜久雄的少年時期,從大阪黑幫家庭到歌舞伎演員成名,以及和歌舞伎世家第二代俊介互為鏡像虛虛實實的過程。至於下冊《國寶》,將更深入描寫歌舞伎演出,觸及日本傳統美學中最高層次的「空」與「寂」,讓人重新思考肉身搏命與文化的交織。
以下,本文筆者將以上冊內容閱讀與思考為主,除概述上冊故事,並整理自身的思考,作為此篇閱讀札記的探索。
一、內容概述
(一)昭和三十九年(一九六四)元旦,新年宴席中,九州黑幫立花組遭到宮地組突襲,立花組從此頹敗,組長權五郎亦在混亂中身亡。其十四歲的獨子喜久雄(背後刺有雕鴞刺青-一種黑幫的符號與印記,並自詡為鳥禽中的「鴞」),隨即在長崎的中學升旗典禮上刺殺宮地組頭目宮地恆三,卻以失敗告終。事後,他被送往大阪歌舞伎世家——花井半二郎家中,自此踏上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
(二)喜久雄與花井家獨子俊介,兩人十五歲相遇,一同在花井半二郎家中學習歌舞伎藝術、求學與生活。兩人一起成長、競逐與相依相扶。演出「雙人道成寺」時一起成名,卻在喜久雄代演「曾根崎心中」時,俊介離家出走。十年後兩人重逢。構成《國寶》上冊的敘事主軸。
二、思考
(一)關係的儀式感——彈額頭
在一次登台演出前,喜久雄邀請俊介將頭靠近,隨即用手指輕彈了他的額頭。這個看似微不足道的動作,卻象徵著兩人之間深厚而親密的情感,對比日後疏離的感慨。
從日常生活、歌舞伎修業、學校課業到舞台演出,兩人幾乎形影不離。然而,當俊介離家出走後,再度同台時,互動中卻浮現出難以忽視的疏離感。這份疏離,來自於兩人截然不同的成長歷程:俊介在離家後學會在野台戲中磨練自己,從凡事講究一流的少主,轉化為能在任何舞台上發揮實力的演員;而喜久雄的成長,則源自父親在黑幫鬥爭中被殺的創傷——尤其是在國中司令台上,冷靜算計、為父報仇的那一刻。
俊介因血緣身分得以順利回歸歌舞伎舞台,歌舞伎世家「血緣」與「非血緣」之間的差異,也無可避免地在兩人之間劃開了距離。「彈額頭」,成為血緣世襲俊介或者永遠無法擁有血緣喜久雄間,再也無法回到過去的表面/兄弟間的親暱情。
(二)血統、世襲與依附
喜久雄曾對俊介說:「真希望能大口喝俊寶的血。」(P171)這句話既殘酷又真實,直指歌舞伎世界中血統的份量。
第二代半二郎所依附的「部屋子」喜久雄,原本只是被看好的一般人,卻在沒有世家血緣的情況下,成為第三代半二郎。這樣的轉折,究竟源自喜久雄無可取代的實力?抑或是第二代半二郎在臨終前,急欲完成「花井白虎」的名號升格——尤其在少主俊介離家出走之際?若是如此,這份承繼,是否同時也是一場精心計算後的幸運?
(三)加害者與恩人的兩面並存
殺害喜久雄父親的「辻村」,彷彿體現了黑道世界中小弟弒兄奪位的慣例。然而,正是這個「辻村」,邀請花井半二郎出席立花組的新年宴,讓花井意外看見喜久雄的演出;也是這個「辻村」,在歌舞伎不景氣時資助喜久雄,使他得以持續走在舞台之路上。
這究竟是大阪黑道所謂的義氣?花井半二郎明知內情,卻對喜久雄說出「以藝決勝負,才是有意義的報仇」(P217)——這句話的深意,是否正是將仇恨轉化為藝術的試煉?而更殘酷的是,喜久雄始終不知道,殺父仇人與人生貴人竟是同一人,反而將復仇對象指向滅門的黑幫宮地組。
(四)花井家第二代後人俊介認為,歌舞伎的穿、吃、玩,樣樣都必須是一流;而部屋子出身的喜久雄則相信,只要站在舞台上,自己是一流的,身邊未必需要一流的條件。(P145)這樣話語看出兩人價值觀、性格及舞台表現的價值差異。孤身以及沒有歌舞伎大家血統的喜久雄,似乎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前行;而俊介則在歌舞伎血統及雍容物質的傳統上養成天生的演出者氣質。即使離家出走,從野臺戲演出,除了技巧更加純熟,生活方式與人際較為練達,加上原有的世襲血統,俊介離家後的成長,似乎讓自己相較喜久雄更有圈內優勢。
(五)大阪萬博在小說中所呈現的時代意義(P171)。
書中不斷提到萬博(1970年),以及萬博期間日本媒體及日本人對萬博的狂熱。萬博似乎對歌舞伎演出也造成影響:經濟起飛、萬博所展示的新世界與傳統歌舞伎之間的對照,使既有傳統(如血緣制度)開始鬆動之外,歌舞伎也因媒體複製性高、即時傳播與年輕女性觀眾的加入而產生變化。另一方面,萬博或許也象徵著日本從二戰戰敗國,再次躍上世界舞台、成為耀眼新星的歷史時刻。
另一方面,日本與世界競逐的「萬博」展示下,是否日本人也會支持相對能代表日本的傳統文化,如歌舞伎,而產生一波追星熱潮?似乎在「歌舞伎」沉沉浮浮的演出市場上,推波助瀾一把。
小結
小說多次刻意點出「大阪腔」與「東京腔」的差異(P283)。
筆者略查閱相關資料後,或許以此簡要分析作結:大阪腔與東京腔,幾乎標示了日本語言中的文化位置。
在《國寶》中,作者多次刻意標示「大阪腔」與「東京腔」的差異,語言不僅作為人物對話的工具,更成為標記其文化位置與身分歸屬的重要符碼。大阪腔所承載的,是地方性、庶民性與身體記憶,貼近歌舞伎作為活態身體藝術的生成現場;東京腔則象徵制度化的標準語言,連結國家權力、文化正統與評鑑體系。
對喜久雄而言,大阪腔既是其生命經驗的來處,也是難以擺脫的身分印記,使他始終被辨識為文化中心之外的存在;而東京腔則以冷靜、抽離的姿態,構成「國寶」之路上無形卻關鍵的門檻。小說藉由兩種腔調的並置,呈現地方文化與國家文化之間的張力,並進一步提問:當源於地方、仰賴身體與師徒傳承的歌舞伎,被推向「國家級藝術」的位置時,是否也同時承受著去地方化的代價?
作者為台東大學兒童文學博士,教育部閱讀推手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