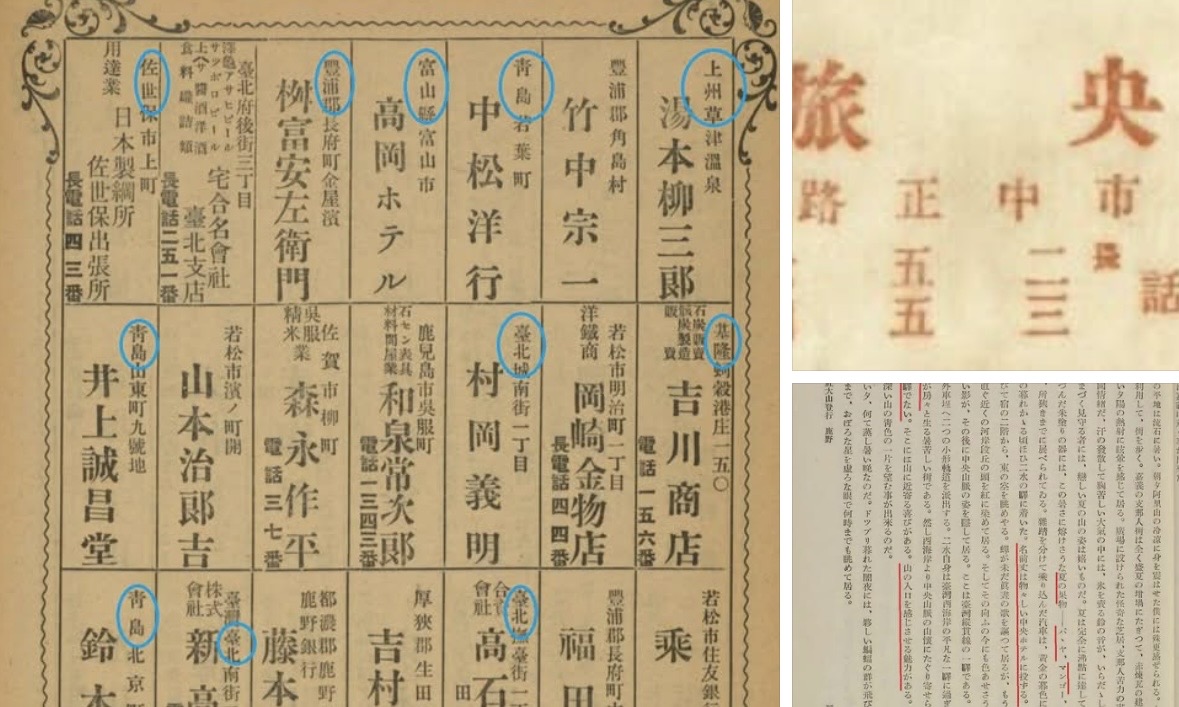圖片為佛光山官網截圖
【鄭功明投稿】「午後的光像細箭,射入房間,也穿透了我塵封的心。」
鏡中的自己靜靜凝視我——
陌生又熟悉,
彷彿一位舊友,也像陌生旅人。
「這軀殼,真的是我嗎?」一個念頭,刺破午後的平靜。
⋯⋯
一念之間,萬法皆幻。
佛陀說:「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
這與量子科學所說的「堅實物質,其實只是能量波動」
有著驚人的相似性。
世間一切相,皆是心念創造出的短暫幻影。
⋯⋯
就在這一念之間,我忽然覺察:
我們都來自同一個源頭,
那本源沒有生死,沒有形體,
也不受塵垢污染;
它不曾增加,也不曾減損,
卻能孕育萬物、映照一切。
而這本源,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真實本貌。」
⋯⋯
只是因為忘記,
我們開始有了各種想法與幻象,
創造出虛假的「我」,
變出了這個有你、有我的世界。
我們看得太入戲,
隨著劇情歡笑、流淚、執著、沉迷;
卻忘了銀幕背後,
所有的一切,只是由我們的意識投射的夢。
我們誤以為自己是觀眾,
卻未曾察覺,
自己正是這部電影的編導——
每一個因果,
每一個境界,
都是本心所展演的情節。
⋯⋯
某一刻,心微微覺醒。
突然發現:
我不只是觀眾,
也是整部電影的創造者。
而一場突如其來的意外,
以無可抗拒的力量,
推開通往內心真相的門。
⋯⋯
「究竟我是誰?」
答案,早已靜靜守候在門後。
⋯⋯
門後的世界,不是外在的風景,
而是一次徹底的揭示:
我們的心,從未失去圓滿,
本來就是佛,
光明自性,本然具足。
⋯⋯
這趟回家之旅,
不是去尋找新的真理,
而是重新認出——
清淨的法身
圓滿的報身
應機的化身
⋯⋯
這是一場從幻夢中醒來的旅程。
這是一場從流浪中歸返的朝聖。
這是一場讓淚水與花開,
同時綻放的——真正的覺醒。
---
「第一部曲:心鏡初現,三身覺醒」
---
1. 宇宙是夢,苦樂是幻
這世間的快樂與痛苦,為何總是來得那麼急,走得那麼快?
快樂如一道閃電,瞬間點亮了黑夜,卻在眨眼間消失無蹤;
痛苦似一場大雨,淋濕了全身,卻終究會停歇。
我們拼命想抓住每一個瞬間,卻總是徒勞無功。
佛法中有深刻的觀照:一念之中有數兆,甚至無量次的生滅。
所謂「念念生滅,念念不住」。
我們的心,以不可思議的速度,不斷生起、又不斷消逝。
一幕幕短暫的幻影,被串聯成片,於是我們誤以為:這是一場真實而永恆的旅程。
「這與量子物理的洞見有著驚人的相似性:在微觀世界裡,堅實的物質並不存在,存在的只是空性在因緣下所顯現的一團能量波動。」
這些能量波動,並非獨立存在,而是由無數因緣的匯聚與消散所組成。當因緣聚合,我們誤以為「快樂」或「痛苦」是真實的實體;當因緣離散,它們便自然消失,無影無蹤。
這種不斷生滅的能量波動,
正與佛法所說的——「萬法唯心造」——相應。
我們的意念,創造了物質。
而物質,只是能量的顯現。
繼續拆解,最終只剩下:空性。
一切只是流轉,根本無所謂實體。
因此,淨空法師說:「所有相皆是虛妄」,正是對這一切最精闢的總結。
無論是歡笑還是淚水,無論是金錢還是名聲,
我們所見、所聞、所觸的一切相,
都只是一場由心念所投射出的幻影,轉瞬即逝。
然而,幻影不是敵人。
它的存在,只是提醒:
別忘了湖水的澄明。
別忘了星空的深邃。
別忘了心底,始終不動的光。
因為唯有照見心鏡,我們才能分辨出,哪些只是虛妄的影像,哪些才是真實的光。
這讓我們深切體會到《金剛經》的偈語:
「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
我們的心,像湖面,像鏡子,也像底片。
它不斷映照,卻不會保留任何一幕。
但我們沉浸在影像裡,忘了湖面的清澈、鏡子的空明、底片的空白。
那超越一切現象、清淨無染的本性,才是我們真實的法身所在。
「回家的第一步,就是放下對幻影的執著,像凝視一汪靜止的湖水,看見其中的澄明。」
---
2. 善意如花,同體共生
當我們的心暫時歸於平靜,那種迷惘感中,偶爾也會閃現出驚人的澄澈。
你是否曾凝視過一朵花?不只是看見它的色彩,而是真正地感受它的存在。
你意識到,它的盛開需要陽光、空氣、水和土壤。
它的每一片花瓣,都承載著大自然的饋贈與時間的流逝。
這就是「一花一世界」的真實體悟。
當我們深觀一朵花,我們會發現,這朵花並非孤立存在。
它的美,是太陽的光、雲朵的雨、泥土的養分、以及無數微生物辛勤勞作的結果。
它與遙遠的太陽、與腳下的大地,與整個宇宙,是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
這份體悟,正是我們報身的顯現。
報身是清淨本性經由無量劫修行所累積的圓滿智慧與慈悲。
它不是一個外在的神佛,而是我們內在光明與善意的具體化身。
星雲大師曾倡導「同體共生」,這與佛法「大而無外,小而無內」的洞見不謀而合:
我們的心可以廣大到包容整個宇宙,但它也細微到可以存在於每一粒微塵之中。
我們是宏觀與微觀的統一體,是彼此相連、永不分離的存在。
這份「同體共生」的真理,正是華嚴帝網鏡的深刻展現。在這面由無數寶珠交織而成的鏡子裡,每一個微小的個體都映照著無盡的世界,彼此相連、互相映照,共同構成了整體的樣貌。
回家的第二步,就是用每一次的善念、每一次的放下,去擦拭心鏡,讓我們的報身之光重新照亮自己與周圍的世界。
在那份無私的連結中,我們才真正體驗到,給予,其實是最大的圓滿。
---
3. 因果是師,妙用是路
既然我們的本性如此廣大無邊,為何我們總是深陷於無窮無盡的煩惱之中?
答案是:我們的心鏡蒙上了塵埃。
我們心中的貪婪、瞋恨、傲慢、愚痴,
就像一層又一層的灰塵,
遮蔽了心鏡原本清澈的光明。
我們誤將鏡中映照出的幻影,窮其一生追逐,以為那是真實的我。
每一場追逐,都形成新的因果,
讓我們更深陷於這場無止盡的夢境與輪迴。
這些「追逐」的念頭,
本身就是一種因緣。
當心與貪婪、瞋恨相應,
便創造出相應的因緣,
讓我們經驗不順遂的工作、受挫的人際。
這不是懲罰,
而是因緣所生、因緣所滅的自然法則。
每一次「不順遂」的境遇,
都是一個示現的因緣,
提醒我們回光返照,
去改變內在的心念,
從而轉變外在的因果。
我們之所以感到疲憊,正是因為我們一直在追逐鏡中的幻影,卻從未停下腳步,去擦拭和凝視這面鏡子本身。
佛的化身,
就像光,照在因緣上,
所顯現的智慧影像。
這份智慧,
正是我在最充滿怨懟的時刻——
親身體會到的。
那段時間,
工作不順,人際受挫,
心中滿是苦澀。
直到有一天,
一位老比丘淡淡一句話點醒了我:
「不要緊,這些都是佛來教你。」
那一刻,我震撼地明白——
煩惱,
其實就是佛的語言。
每一次不順遂的境遇,
都是因緣所生的示現。
提醒我們回光返照,
溫柔地拂去心上那一層塵埃。
當我們學會——
把每一個因果都視為一堂功課,
把每一個境界都看作化身的指引,
便不再是因果的奴隸。
而是因果的主人。
---
「第二部曲:淚水洗淨,無常開出智慧花朵」
> 然而,所有關於夢與幻的體悟,若沒有落在真實的生命經歷裡,仍舊只是紙上的智慧。真正讓我看見佛法骨血的人生功課,來自於最深的失去。
今年的父親節,我沒有準備禮物,也沒有慶祝的歡聲笑語。我一個人靜靜地坐著,看著窗外,思緒卻飄回到許多年前的那個時候。那時,最愛我的父親才剛離世不久。
我獨自一人,行走在中港大排旁,內心充滿了海嘯過後般的死寂與荒蕪。那段時間,世界的喧囂似乎都與我無關,只剩下捧著他的骨灰,看著照片上他熟悉又陌生的笑容時,那種被巨大悲痛吞噬的感覺。
直到那一刻,我才真切體會到,佛法中那句**「諸行無常」**,早已超越了高深的理論,化為我心頭最錐心的刺痛。
痛,是這場旅程的起點。它讓我不得不問自己:這具會老、會病、會死的肉身,到底是不是我?如果連最親愛的人都無法永遠留下,那麼,這世間還有什麼是真實不滅的?
當我面對無常,我才明白,我們所執著的一切,無論是名聲、地位、成就,甚至是那些最美好的回憶,都只是這場大夢中的幻影。它們美麗,卻也轉瞬即逝。
父親的離去,就像一記重重的鐘聲,在夢中敲響,催促著我該回家了。
1. 無常之痛,喚醒青春幻夢
在我最深的哀愁中,走在中港大排,我無意間看見了右邊那棟熟悉的社區大樓。
那不只是棟建築,更是一道時光隧道的入口。一個名字,像一把古老的鑰匙,輕輕開啟了我塵封已久的記憶之門——
那裡,曾是國中同班同學吳奇隆的家。
剎那間,我從此刻的悲痛,被拉回了那段熱血沸騰的青春時光。
我依然記得地下室的柔道館裡那股獨特的氣味,混合著汗水、榻榻米和老舊木頭的味道。
那時,我與國小同班的賴祥蔚教授,以及國中同班的吳奇隆一同練習。祥蔚教授文武雙全,他總是像個可靠的大哥哥一樣照顧我們,他的眼神總是很堅定,彷彿在說:「別怕,放手去搏鬥吧。」
我們三人在柔道墊上揮灑汗水,每一次摔倒、每一次起身,都發出沉重的聲響。
比賽時,場邊的喧囂與教練的吶喊聲,都被我們在墊上的每一次搏鬥所掩蓋。
當裁判舉起勝利的手,那種全身肌肉痠痛卻又熱血沸騰的興奮感,至今想來,依舊鮮活。
就在這份回憶的牽引下,我的腳步不知不覺地走到了塭仔底濕地公園。
我靜靜地坐在湖畔,看著眼前鳥兒啼叫,花兒噴香,想起了多年前,我與父親也曾一同到此散步。
那時我們天真以為,父親會一直陪伴在身旁,青春的笑聲會永遠不散,所有的人與事都會如當下般恆久不變。
卻沒想到,時間像湖面輕輕滑過的一陣風,轉眼便把最溫暖的場景吹散,只留下回憶在心底泛起漣漪。
也就在這樣的對比裡,我才真正懂得——原來,所謂「無常」,不是冷漠的奪走,而是提醒我們:珍惜每一次相聚,因為它本就短暫。
父親的離開,讓我看清一件事:我們一直以為的「家」,不是某一棟建築、某一張餐桌,而是那份能讓心安住的歸屬。
而當外在的一切都隨因緣而變動時,唯一能依靠的「家」,其實就在我們的本心之中。
回家的路,並不是往外尋找,而是在一次次面對失去的時刻,慢慢轉身,回望那面塵封已久的心鏡。
命運似乎總在我最措手不及的時刻,用不同的方式提醒我:人生如夢,唯有心是真實的。
---
2. 神識離體與佛號共振:法身自念
也正是在這無常的幻夢中,我第一次親眼見證了超越肉體的真實。
國中時,我與朋友從輔仁大學後門走在回家路上。
一輛疾馳而來的摩托車,毫不留情地撞上了我。那一瞬間,我被巨大的衝擊力拋飛,但更不可思議的是,我的意識竟然在那一刻,輕盈地脫離了肉身。
我像是從一個沉重的繭裡破繭而出,變成一道光,靜靜地懸浮在空中,俯視著地上的自己。那具倒在路旁的身體,彷彿一件被遺棄的舊衣。
周圍的世界,燈光、樹影、車輛,一切都如幻影般透明虛幻。那時,沒有恐懼,只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寧靜與釋放。
那次意外,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看見宇宙真相的驚鴻一瞥。它讓我真切地體會到,這具會受傷、會疼痛的身體,並不是我。真正的我,是那個能見、能知、能覺的覺性,是那個超越生死、不生不滅的法身本體。
這份對真心本性的體悟,讓我深刻明白——死亡並不是終點,而是一扇門。穿越那扇門的,不是脆弱的血肉,而是永恆清明的本心。那才是真正不生不滅的『家』。」
那份對真心本性的追尋,在我當兵時的修行中,有了更深刻的印證。
那一晚,當兵的寢室,特別寂靜。
我誦完《心經》,雙手合十,開始持念: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忽然,心中升起一絲懈怠──想要停下來。
然而,令我震撼的是——
我的嘴巴依然在動,
耳朵依然聽到佛號,
心識與整個身體,像被無形的力量牽引,
佛號依舊在念念相續,
根本停不下來。
那一刻,我深切體會到:
念佛,像按下生命電影的暫停鍵。
一念之中,妄念生滅——
數百兆張底片閃爍,
數百兆張底片消逝,
數百兆張底片再生,
幾乎吞噬覺性。
然而,當佛號的頻率與心念合一,
影像停止流動──
我看見底片的本質,它沒有真實的動,只有虛幻的相——空無自性。
佛號,就是那聲,
將我從幻夢中喚醒的光。
那個「不想念佛」的念頭,
在佛號的洪流中,瞬間化為泡影──
如雪入火,
如露入海,
消失無痕。
我才明白——
這已不是「我」在念佛,
而是法身自念,宇宙自念。
念佛,不只是嘴巴的功夫,
而是心與佛,在同一個頻率中共振。
佛號,就是我自性的呼喚。
當我心念「阿彌陀佛」的同時,
忽然轉變成——
「我是阿彌陀佛,阿彌陀佛是我」。
那一刻,我不再是渺小的我,
而是與宇宙同體的廣大自性──
原來,這就是法身的顯現。
> 心歸處,佛即現。
佛現處,家即在。
這兩句話,並非刻意想出,
而是在一次次念佛中,自然而然浮現的真實體悟。
念佛,不是靠嘴,而是靠歸心。
心有所歸,佛性自然顯現。
而那個「家」,就在與佛心合一的寧靜中。
我觀想阿彌陀佛的法相,
佛號的聲音,如光環繞佛身。
在那無聲的共鳴裡,
我不再是孤單的念佛者──
而是——
「我念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念我」。
那一刻,我深切體會到:
佛號,不只是一句聖號,
更是一封穿越時空的家書,
喚醒我內心深處──
那份與佛無二的本來面目。
心與佛,
眾生與佛,
本是一體。
無須尋求──
已然圓滿。
---
3. 慈悲之流:觀音的甘露與同體大悲
前文提到,「報身」是我們內在光明與善意的具體化身。而這份慈悲,也在我生命中以極為殊勝的方式顯現過。
在同一個夜晚,當我持續靜坐並將佛號轉為持誦《大悲咒》時,一個更為廣大、慈悲的境界隨之顯現。
寢室的風扇嘩嘩作響,那本該是擾人的噪音,但那天,我感覺自己正緩緩遠離這個世界。周圍的一切,連同桌上的書、床邊的雜物,都退入一層淡淡的霧裡,變得模糊而遙遠。唯有我口中流出的《大悲咒》,一句句,清晰得不可思議。
它們不像是我的聲音,更像是從我心底最深處,穿越了無盡時空而來——古老、慈悲、無止境。
忽然間,我的頭頂正中央,彷彿被一隻溫柔的手輕輕開啟了一道門。沒有任何疼痛,只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輕盈。接著,一股清涼如露的甘泉,緩緩傾注而下,從我的頭頂,流過眉心,經過胸口,最後灌滿全身。
那不是水的觸感,而是一種帶著無邊慈愛的能量,**像八功德水般自頂而下、清涼遍體,**所到之處,我的焦慮軟化了,憤怒消融了,所有的疲憊都被輕輕抹去。
我無法抑制地淚流滿面。不是因為悲傷,而是因為那種久別重逢的感動,像是個在大雨中流浪了很久的孩子,終於被母親溫柔地擁入懷中。
那一刻,我真切地明白:世間的快樂,無論是美食、華服、動人的音樂,甚至是愛情的甜美,都只是轉瞬即逝的煙花;而此刻湧出的這份法喜,卻像永不枯竭的泉源。這份清涼,不是來自外在,而是觀世音菩薩無盡的慈悲,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親自為我洗滌內心的塵垢。
在清涼與淚水的交織中,「我」心與萬物合一。我不再只是那個持咒、流淚的自己,而是與那股慈悲之流融為一體——廣大,無邊。
我深切體會到,心,原來可以像虛空一樣廣闊,能容納一切,也包容一切。
在那一刻,我的意識被擴大,無遠弗屆。
我將這份清涼與愛,觀想成一道光,照向所有沉淪在苦海中的眾生。
我觀想那些與我一樣,因無常而哀傷的心;觀想那些被貪、瞋、痴所困,無力掙脫的生命。
當我這樣觀想時,「我」的界線開始融化,我能清晰地感受到所有眾生的心念。
那些喜悅或痛苦,都如同大海表面起伏的浪花,在我廣闊的心海中顯現。
我能「見」到這一切,卻不被任何一朵浪花的情緒所捲入。
這份超越時空的自由,讓我深切體會到「無緣大慈,同體大悲」。
這份慈悲不是靠著頭腦去想「我要去救誰」,而是從本心自然湧出的一道光明,照亮了所有與我相連的「浪花」。
我明白了,觀世音菩薩的慈悲,不是外在的神佛,而是我內在報身的覺醒,
一種與宇宙萬物無私連結的本能。
這份連結,是如此溫柔而堅定。
一個強烈的念頭升起:我好想去救度所有沉淪在夢中的眾生!
然而,就在這個悲願升起的同時,一個更深的體悟也隨之浮現——其實,根本沒有一個「眾生」可以被我救度。
當我的心回到虛空,我與眾生的分別心便不復存在。
我們可以將我們的心性比喻成一片浩瀚無邊的大海,而世間所有的物質、情感、甚至我們所執著的「我」,都只是大海表面短暫生滅的浪花。
當我看到另一朵浪花快要消散而升起悲憫時,智慧也同時告訴我——世間的一切,包括我們認為堅實的物質,都如同浪花一樣,並非真實的存在。
浪花之間並沒有一個獨立存在的「你」和「我」,我們都是大海的一部分。
我懂了——眾生的解脫,不是依靠外在的拯救,而是必須「跟我一樣回歸自己的本性」,才能真正從這場大夢中內在覺醒。
我們的心性宛如浩瀚無邊的大海,寧靜而深邃。世間萬象、眾生情感,乃至那執著的「我」,都不過是大海表面上瞬息萬變的浪花。浪花升起時波光粼粼,消逝時歸於寧靜;它們雖美麗,卻短暫而無自性,無法獨立存在。
這正是佛法所揭示的真理: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我」與「你」的分別,也只是心識中的波動,並非永恆不變的實體。
當我們深深體會到浪花與大海的合一,明白「我」不過是大海的一朵浪花時,悲憫與慈悲的心便自然流淌,這不是基於分別的「救他人」,而是來自對一切生命本質無二無別的深切覺知。
這份覺知猶如清晨的曙光,穿透了無明的迷霧,讓我們明白:真正的解脫,不在於外求救贖,而是內在的回歸——回歸那無邊無際、永恆不變的心海。
於是,那份從心底湧現的悲願,不再是對一個「他者」的執著,而是對整體生命的慈悲流動,是與宇宙本性同體的真實展現。
這份「想救度眾生」的心念,以及隨之而來的智慧洞見,就是化身的具體顯現。它不是一個單純的行動,而是一種應機而生的慈悲智慧,引導我們在回家的路上,不僅自己覺醒,也成為照亮他人的燈塔。
正如大海擁抱每一朵浪花,我們的心也擁抱著萬法無我、同體共生的無限智慧與慈悲。
---
結語:在佛的三身中醒來,不再流浪
這趟旅程,最終的啟示不是找到一尊佛,而是**「認回自己」**——認回那個在淚水中醒來、在佛號中圓滿的自己。
我終於明白,父親的離世,不是生命的終結,而是我修行路上最深刻的啟示。他用自己的無常,為我證實了永恆的真實。
回家的路,不遠,就在我們的腳下。這條路,不需要向外尋找,而是向內回歸。它藏在我們每一個念頭裡,每一次呼吸間。
當我們念佛、觀照、真心放下,我們便已在回家的路上。
這條路上,有淚,因為我們看見了無常與幻滅;
這條路上,也有花,因為我們最終在佛號中,看見了自己本來的光明。
然而,在這條路上,我仍不斷追問:
「我究竟是誰?我又要去哪裡?」
這個問題,在生命的旅程中如影隨形。
其實,在軍中修行的日子,我曾短暫觸碰過這個答案——
當佛號攝住六根,心境澄澈如鏡,我看見那一瞬的光明。
後來持誦《大悲咒》,又體驗到甘露清涼、法喜充滿,
彷彿極樂世界的八功德水,在身心之中流動。
然而,那些境界只是驚鴻一瞥,
如旅人遠遠看見家鄉的燈火,
提醒我——路就在前方。
我,是那面清淨無染的心鏡,是那道映照一切的圓滿光明,
更是那股與萬物同體的無盡慈悲。
這場關於生命的旅程,最終的目的,
從來不是抵達某個遙遠的彼岸,
而是回到我們的家。
而這個「家」,正是我們圓滿的法身、報身、化身。
我們的迷失,不是走錯了路,而是忘了自己本來在哪裡;我們的回家,不是重返舊地,而是認回自己本是誰。
這一切的親身經歷,無論是神識離體的洞見,還是念佛、持咒時與佛菩薩的共振,最終都指向一個核心的真理——我們無須向外求,因為我們本來就是佛。
這份圓滿的本性,可以最貼切地被比喻為一面莊嚴無盡的華嚴帝網鏡。
這面鏡子不僅是心性的比喻,更是佛法中法身、報身、化身三者圓融無礙的動態展現。
法身,是鏡子本身。它清淨無染,能映照一切,卻不被任何影像所染。這就是我們不生不滅的清淨本心。
報身,是反射的光芒。
我們的一個善念,就像帝網中的一顆寶珠被撥動。這顆寶珠並非孤立,而是與無數寶珠在因緣中相互連結。
因此,其光芒將透過無限反射,照亮整個宇宙。這份光芒,正是我們圓滿的智慧與慈悲;它透過無數因緣的流轉,具體而鮮明地顯化出來。
化身,是鏡中的影像。
那些在我們生命中出現的人、事、物,都是因緣成熟時所顯現的映像。它們以不同的形式,應機而現;為的,就是引導我們擦拭心鏡,看清——因緣所生、因緣所滅的真相。
因此,這不僅僅是我們心性廣大與微細的描述,更是心包太虛與一念三千的真實體驗。
當我國中時,因意外而神識離體,變成一道光,輕盈地懸浮在空中,俯視地上的自己。
那一刻,我真切地看到,那具會受傷、會疼痛的肉身,就像是這面華嚴帝網鏡所映照出的影像。而我能「見」、能「知」的覺性,才是那面超越影像、清淨無染的鏡子本身。
這份不生不滅的清淨本體,正是法身的體現。
這面莊嚴無盡的華嚴帝網鏡,正是因果法則運作的動態舞台。
我們心中的貪婪、瞋恨、傲慢、愚痴,就像是一層層厚重的灰塵,蒙蔽了這面鏡子,讓我們無法看清它原本清澈的光明。
於是,我們誤將鏡中所映照出的幻影視為真實的「我」,窮盡一生去追逐、去佔有。每一場追逐,都形成了新的因果,將我們更深地困在這場無止盡的夢境輪迴中。
然而,當我們的心鏡被擦拭乾淨,便能看見這面鏡子真正的運作方式:
你的一個善念,就像一個鏡面的光芒,會被其他所有鏡面接收並反射,影響著整個重重無盡的因果網絡。
你的每一個起心動念,都像在帝網中撥動一顆寶珠,其影響將超越時空,反射到整個宇宙。
同時,當我們凝視其中任何一個細微的反射點,我們會發現——這個點中又包含著無數個更小的反射,無止盡地延續下去。
這正象徵著,我們的心性不僅廣大到可以包容整個宇宙,也能細微到無所不入,與萬事萬物的每一個細節都緊密相連。
當我們學會將每一個因果都視為一堂功課,每一個境遇都看作化身的指引,便不再是因果的奴隸,而是因果的主人。
修行,就是去覺察這些因果的動態,並選擇在鏡面上投射出更清淨、更光明的影像。
因此,當我持誦《大悲咒》時,感受到那股與宇宙同體的清涼甘泉,以及「想救度眾生」的悲願。
這份慈悲,就不是對一個「他者」的執著,而是源於這面帝網鏡的全息本質——我看到所有眾生都與我相連,他們的苦樂,就是我自己的苦樂。
這份「無緣大慈,同體大悲」,正是從我內在的報身中所流露出的圓滿慈悲。
最終,這一切都指向一個核心的真理——一即一切,一切即一。
當我們念佛,我們不再是孤單的個體,而是與宇宙同體的廣大自性。
在那一刻,「我」與「佛」、「眾生」與「佛」的界線都消融了。
如果硬要用一個畫面來比喻,或許可以說:
法身,像無邊的天空;
報身,像天空裡千變萬化的雲彩;
化身,則是化成雨水落下,滋潤大地眾生。
天空、雲彩、雨水,其實從來不是三個分離的東西,只是同一份存在的不同展現。
就像我們的心,也同時具備了清淨的本體、光明的智慧,以及隨緣流露的慈悲。
這聲佛號,不只是聲音,更是我們與宇宙本性、與一切眾生同體共生的莊嚴印證。
念佛、持咒、誦經,
都是帶領眾生回家的殊勝法門。
它們如三把鑰匙,
分別開啟我們內在的本性、慈悲與智慧。
念佛:
直通心源的捷徑。
喚醒本自具足的佛性,
讓我們認回自己本來的面目,
從輪迴大夢中徹悟,
超脫諸苦。
持誦《大悲咒》:
開啟無邊慈悲的法門。
心與觀世音菩薩的願力相應,
澄淨身心,
在苦海中伸出慈悲之手。
誦讀《心經》:
開啟般若智慧的法門。
洞見世界的虛幻本質,
放下一切執著,
照破無明長夜。
雖然法門各異,
最終都指向同一個家。
當我一步步走過痛苦,
看清無常,才明白——
回家,不在遠方,
而在每一次凝視心鏡的片刻。
心鏡提醒我:
萬相皆幻,唯有本性不動。
無常提醒我:
再深的悲傷,也只是因緣一合一散。
佛號提醒我:
真正的家,
一直都在心中,
從未失落。
原來,我不必再流浪。
當我念起——
「阿彌陀佛」,
這聲音穿透了悲傷,
也喚醒了心底最深的光。
那光,
不是來自外界,
而是本心本佛,
這聲佛號,
是開啟本心淨土的鑰匙。
原來——
此心,本即淨土,
從未離開,也無須尋覓。
作者為新北市新莊區居民
●投稿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