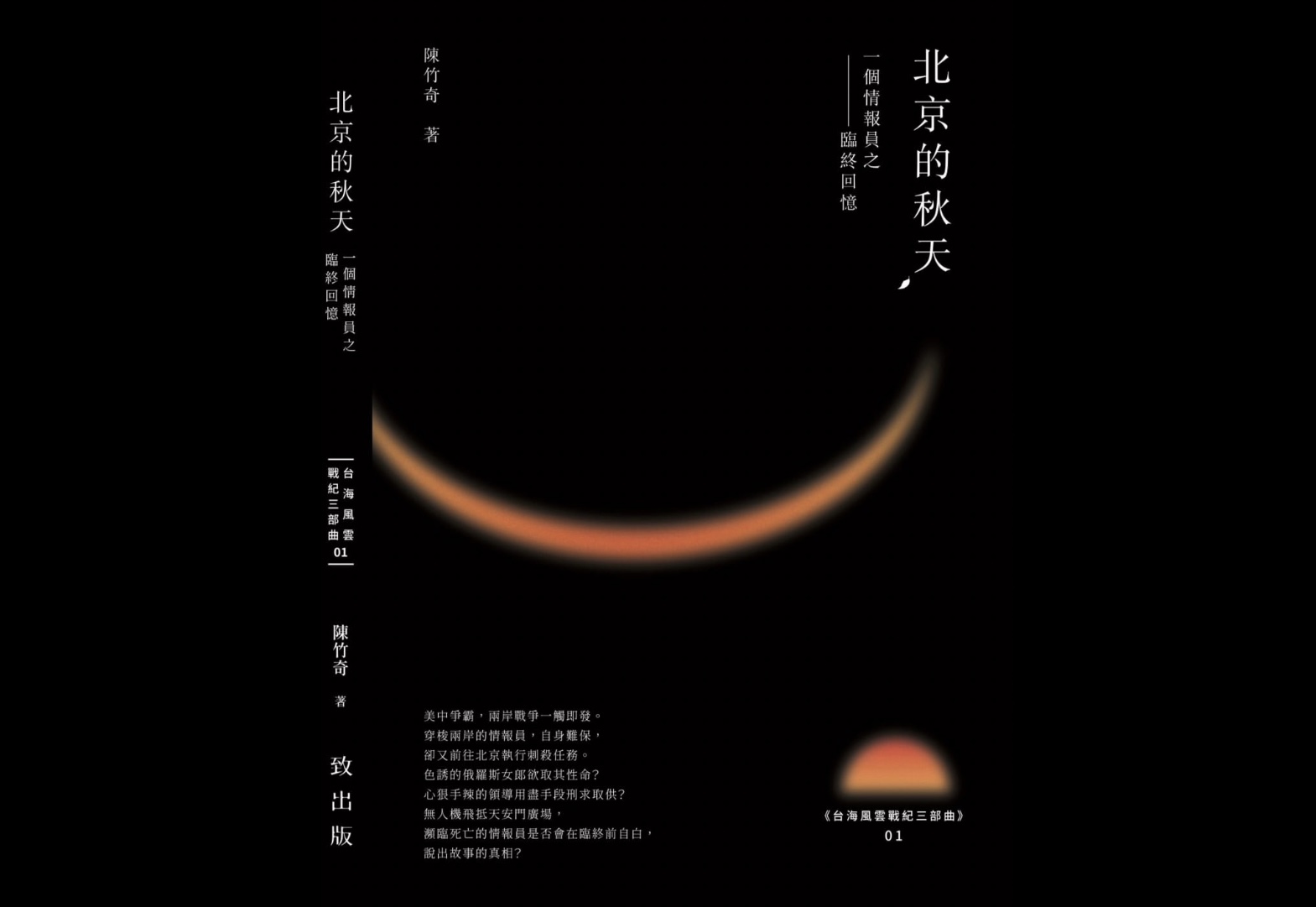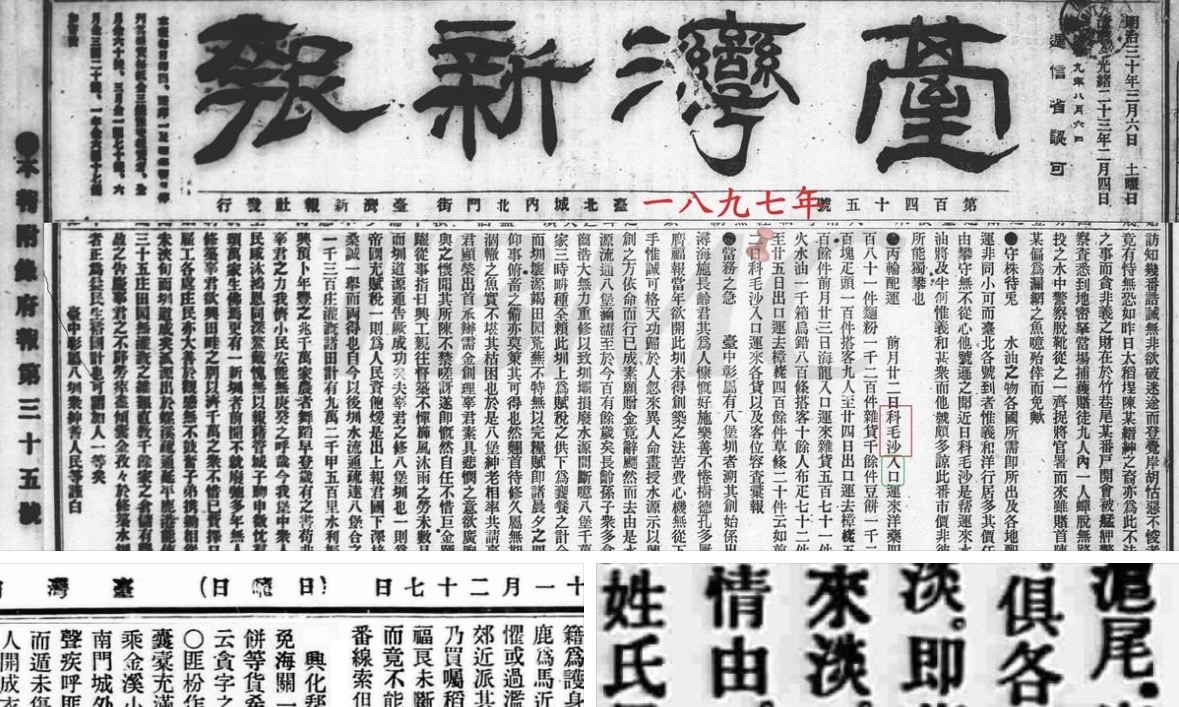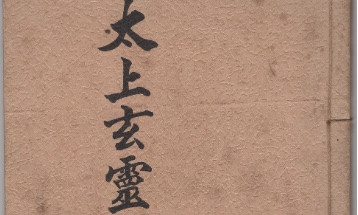【黃愛真閱讀專欄】現實生活中,女性往往因為社會、文化與自我的期待,不斷內化象徵父親的社會秩序,調整自己的語言、服裝、姿態等身心狀態,來吻合環境期待,成為一種觀看的「景觀」:「男性觀察女性;女性則注意自己被觀察。…她把自己變作對象–而且是一種極特殊的對象:景觀。」(《藝術觀賞之道》,商務,頁51。)。遊走東亞與東南亞的國際諜報小說《北京的秋天》(致出版),女性角色具體而微地體現了男性主角「我」,看待這些不同東亞文化與區域間關係,也就是主角「觀看」的在地異國風情,投射的家國關係或者自我處境。
一般文藝理論對於女性做為一種「景觀」,多指涉女性如同物件般展示,成為被「觀看」的標的物。然而,筆者在此,提出《北京的秋天》裡的女性,除了與異國風情縫合,旅遊過客隨意瀏覽的「景觀」與神祕幻想,隨著小說逐漸深入主角「我」的任務及「我」是誰,看似景觀的女性角色,逐漸擺脫表象,成為主角「我」的隱喻,或區域關係間的象徵位置。在此,就讀者而言,女性仍作為一種映照出男性角色「鏡像」的景觀。或者,當主角「我」換喻為象徵性「女性」角色,即使現實的性關係仍處在主動位置,在區域與區域間,也仍然如同女性般被「閹割」。(或者,反過來說,區域關係裡的「我」總處在「虛度時光,一種假象」(摘自小說內文)的閹割位置,才使得「我」非得在東亞或者南亞各區域間獵豔,透過真實的女性軀體,證明自己仍是男性英雄般的存在?如同文中常自比的諜報007?)
《北京的秋天》女性角色,如杭州小姑娘、雅加達單親媽媽等在地無名女性,她們的面貌等同都市景觀,主角一親芳澤所在,「我」透過女性「深入」城市、隱沒在城市內裡;著墨較多的小紅、小趙,如同小貓小狗等具有大致的名字,性格稍具輪廓但模糊不清,呈現不具臉孔的中國某些區域大致女性典型,其中山東大妞小紅對來自小島小國主角「我」的依戀,兩者關係似乎具有某種不對稱體型相處的杆格、曖昧、「我」的自戀,或者無法征服卻又無法抗拒(然而,「我」很明確知道,他過於龐大而不適合「我」),藕斷絲連的區域間關係隱射?
這些沒有名字或者僅具有大致特徵的女性,或許我們僅能稱呼他們為一種在地景觀或者別有目的的用途,用意可能在於呈現主角「我」的觀察或隱沒,如同「我」也沒有名字,僅一個代號/代名詞存在,這些女性角色,如同「我」在區域關係任務間,同樣被放置在「模糊」的角色?在此,「我」看似也和那些女性,沒有什麼不同了。(在別人眼中,被觀看的「我」的面貌也不清楚,如同這些女性。不同的是,這些是「我」的「表演」,刻意安排的行為。「我」有自己的目標。女性在此,成為城市景觀下「我」最適當的掩護?)
另一方面,兒少文學中,作者常設定某種物件或者生物,表現主要人物內在性格,如大家曹文軒的小說《青銅葵花》(小魯出版),作者細密描繪牛的一舉一動、牛與主角的互動,以牛體現主角牧牛童的內在特質;又如「哆啦A夢」中哆啦A夢作為大雄依附幻想中「夠好的母親」(「客體心理學」的一種讀法),觀者從大雄與「夠好的母親」互動裡,得以看見大雄外顯行為的內在需求。《北京的秋天》裡的女性,如同主角「我」的另一個心靈分身,表現或投射主角處在多重位置間的內心小劇場?例如,代號「五月」與「喵」的女性?
至於其他女性,如,主角「我」/島國的代表,對日本的態度與觀感,展現在與日本女性友人真澄間的相處與小小幸福感受。俄羅斯如貓一般神祕的女性,則常常是諜報電影中的刺激美麗女「相手」(日文漢字),這位俄羅斯與中國混血妓女,在小說中從無名女性脫穎成為讓主角「我」恐懼的諜報對象。女性的「無名」,似乎映照「我」而更讓人產生「無以名之」、「琢磨不定」的驚恐。
小說中惟二清晰「可見」,具有力量、擁有自己名字的女性:慈禧與翁山蘇姬,但是在男性的歷史評價中仍帶有爭議。以翁山蘇姬為例,緬甸軍政府這些將軍沒有一個不是翁山將軍昔日的麾下,他們不敢也不願殺害翁山蘇姬,並非他們沒有能力,更不是沒有權力,而是翁山蘇姬是從小他們看著長大,翁山蘇姬掌權不久,他們以及後續的將軍們重新奪回政權,他們依然沒有殺害翁山蘇姬,翁山蘇姬如同過去一樣被軟禁,就像奪回政權,他們依然沒有殺害翁山蘇姬,翁山蘇姬如同過去一樣被軟禁,就像緬甸這個國家依然被凝固在過去的時間一樣。(小說內頁)
女性在巨大的歷史衝鋒陷陣,依舊被放回男性將軍凝視下「小女孩」位置;國家歷史如線性時間,不斷前進,回眸統治者翁山蘇姬時代,國家時間如同回溯凝止在統治者那一刻,一種不斷回去,永遠循環,屬於女性的圓形時間。
作者在《北京的秋天》女性書寫,從文字表現及敘事表達,極其溫和。作為男性書寫的縫隙,仍可見女性作為幫襯、烘托男性角色或者對照的存在。
作者為教育部/衛福部醫事人員性別講師、台東大學兒童文學所博士
封面圖檔:陳竹奇提供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