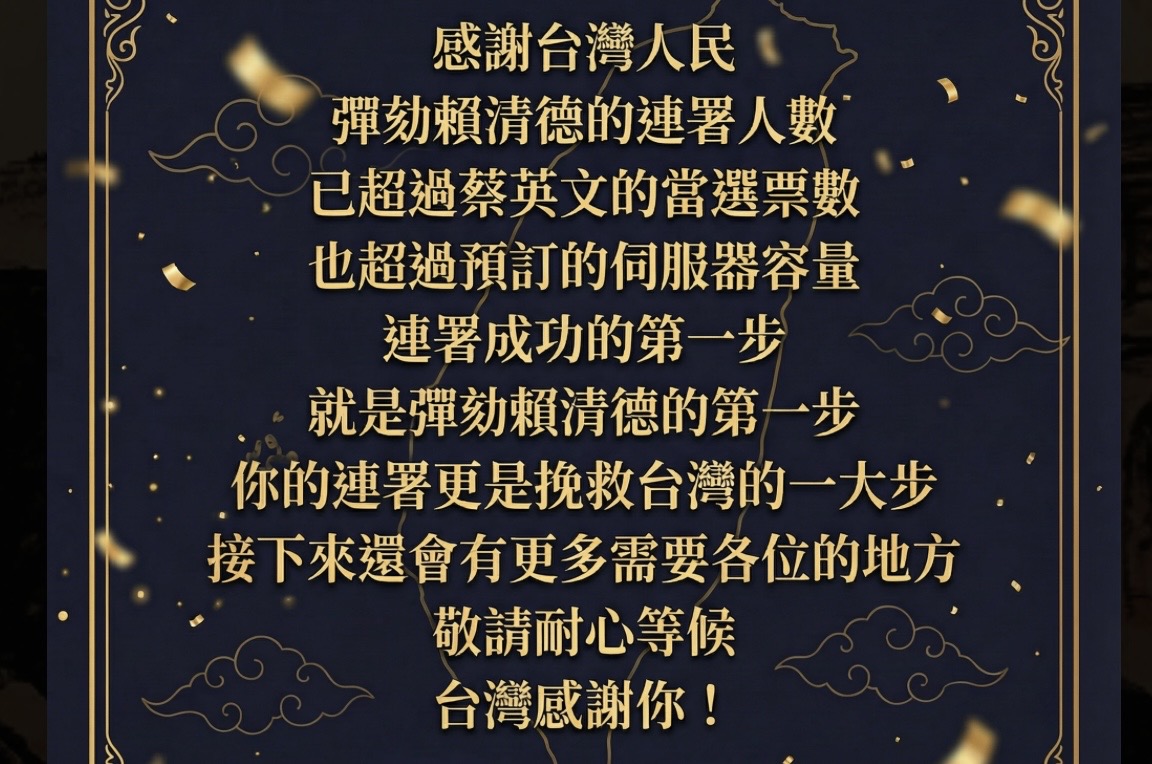照片取自中選會官方網站
【聚傳媒奔騰思潮專欄】大罷免的大失敗,暴露了臺灣民主的兩個本質問題,一個是體制上無法正常運作的少數政府,一個是使人民長期陷入混淆的國家認同。二者都因為政者無意面對而不時爆發衝突,也將因繼續迴避而再起。我剛談過前者,這裡再簡單說說後者。
國家認同的混亂,當然和1949年起的國共隔海分治有關。在終止動員戡亂、以憲法增修條文取代臨時條款以前,我們所稱的國家指的就是憲法本文描述的主權範圍,因此當時主張中華民國不包含大陸的,可能會被認為構成意圖分裂國土。民主化階段,國民黨和後來建黨的民進黨對於國家的想像明顯不同,在1990年有點類似當年政治協商會議的國是會議,用德國憲法學的概念來說,便是為「制憲力」的發動在作準備,當時對於借鑑二戰後在聯軍占領下的西德地區制定的基本法一樣,把中華民國改變定位為主權與統治權分離的「分裂國家」,而不再是暫時分裂的內戰狀態,已有相當的共識,故翌年通過第一屆國大代表制定的第一次憲法增修條文,就已經建立在原憲法所定中華民國的主權範圍不變、但在自由地區行使的國家統治權已不及於不能參與定期選舉的大陸地區,隨之制定的兩岸條例第2條更忠實的對於主權和統治權的土地和人民範圍做了具體的界定迄今,因為憲法增修條文共修了7次,政權也已在國民黨和民進黨間反覆輪替,對於國家定位的決定卻從來沒有一字更動。
所以我們的國家始終還是中華民國,臺灣只是統一前中華民國統治權所及的「地區」,臺灣地區既以建立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自居,對於未能參與此一秩序的地區和人民便無法通過其參與選舉而取得統治的正當性,臺灣地區定期認可的中華民國政府當然也不再有對對岸統治者實施「戡亂」的立場,但同一主權下的兩岸人民當然可以保持交流。同樣可以邏輯導出的是,臺灣地區和大陸地區的人民既不能以「國籍法」區隔,只好以「戶籍法」標定統治權的範圍。為處理兩岸人民交流事務,中央只能設置大陸委員會,而未把兩岸統治權間的互動事務交給「外交部」辦理,更多的細節這裡只能略過。
但因政府已經帶頭在許多地方淆亂憲法設下的清楚定位,中學社會、公民課不講清楚,連法學院的憲法課也多跳過不論,我只能一再提醒國人去仔細讀讀有最後憲法解釋權的大法官是怎麼解析這麼敏感的部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解釋或判決偏離上述分析的國家定位,不論是哪位總統任命的大法官。有興趣的讀者不妨讀一下全由陳水扁總提名任命的15位大法官做成的第618號解釋,包括後來又出任司法院長的許宗力大法官,在該解釋對於憲法上的兩岸關係,以及入籍臺灣的大陸人民,在定位上都精準到沒有一字出格,而且沒有任何不同意見書。同樣前兩年普通法院在處理上海青年不幸在旅遊臺灣時罹難的國賠案時,認定他不符合國賠法上「外國人」的概念。在在說明,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法官對於國家定位的說文解字除了嚴守憲法以外,別無選擇。就如法官可以不喜歡很多法律的內容,但他只能依法審判,否則法治如何不立刻崩盤?
我過去也多次以國是會議與兩次修憲參與者的身分談憲法的「統獨政策」。認為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5項已明確排除脫離中華民國而獨立的選項,但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自由地區」)的堅持下,任何中華民國的統一政策也都不能牴觸此一基本原則,這也是增修條文不同於臨時條款的另一重點,即只在引言中提到「為因應統一前之需要」,對政府完全未設追求或完成統一的誡命,更不要說有分裂終期的限制。因此只要嚴守前面提到的基本國家定位,政府反映民意而訂定的兩岸分合政策,憲法已經保留了最大的空間。就人民對於國家認同的選擇方面,在自由民主憲政秩序下本來就應該受到充分的言論自由保護,不論人民、法官或政黨都可以有不同的國家認同,包括完全摒棄國家的無政府主義;只是在憲法改變此一定位之前,法律體制即只能一體遵行才有秩序可言,這本來就是憲政國家的本質,我相信也是當初民進黨願意接受此一方案的重要原因。
從這個角度來看兩岸關係令人眼花撩亂的最新發展,乃至抗中保臺和親中賣臺變成這次大罷免所以從小變大的主要理由,我們要做任何價值或法律的判斷,恐怕都不是僅憑上述的憲法定位就能找到答案,兩岸交流的管制,和戰之間的抉擇,都還有很多民主論辯和政策選擇的空間。這裡構成更大障礙的,恐怕還是資訊的混亂和成見的干擾。諸如突然加大對陸配管制的力度,旅遊的限制,以及軔性組織對武統引路人的猜忌,為鼓吹團結而把百分之98的漢人在官方文書改稱「其餘人口」,他如退將對大陸軍力大躍進的亢奮,大陸學者對臺灣統獨膠著的咄咄逼人,小粉紅和綠衛兵的相仇以沫,網紅來來去去,由綠轉紅又由紅轉綠,恐怕是我們這個少見的國家狀態在這樣誇張的數位通訊時代,很難保持耳根和大腦清明的原因。但我始終相信一些基本的人性,和民主體制培育的基本寬容,讓我們還是比較容易保持一定程度的不惑。親眼看到大陸轉向改革開放以後各方面的突飛猛進,我也相信,只要站穩「兩岸同為中國」的立場,堅守「臺灣的土地和人民為中國一部分」的憲法立場,海峽的戰爭風險已可降到最低。兩德的經驗也告訴我們,冷戰時期地處北約和華沙集團第一線,經常有四萬左右東德間諜四處活動的西德,並沒有妨礙他們坐下來簽訂和平協議,且在深厚的歷史文化基礎上,統一一旦條件成熟,政府即使想擋也擋不了。但什麼時候堪稱成熟,各人可以有自己的底線。於我而言,僅僅不能選舉主要決策者,沒有暢議中央的自由,任何人可以不明原因半夜失蹤等等,就完全沒有啟動統一談判的條件。
扯了這麼多,我想說的是,從以「親中賣臺」為總體理由的大罷免如此徹底的槓龜,其實也可看到在民主體制問題外,臺灣人民反過來喚醒政府要正視另一個本質問題:停止繼續玩弄國家的憲法定位。如果賴總統和他所領導的民進黨一定要貫徹他們不同於憲法的國家認同,當然是大家都要尊重的言論和思想自由。拜託請開始準備修憲修法,也請千萬要把人民在混亂和清明之間所想表達的國家認同考量進去,包括戰爭風險的計算,不要僅僅用沒有任何前提的認同民調就拿來做決策的基礎。一個很簡單的反測就是,如果這些民調代表的真是絕大多數人民的國家認同,為什麼民進黨到了完全執政都還不提修憲,連只需要多數立委支持就可以修改的兩岸條例都不做任何更張?誰有權利把人民對戰爭的恐懼抽離,以最「純粹」的國家認同作為統獨決策的基礎?果真如此,人民通過投票要表達的真的就是:停止再打統獨嘴炮了!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講座教授、前司法院大法官並任副院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