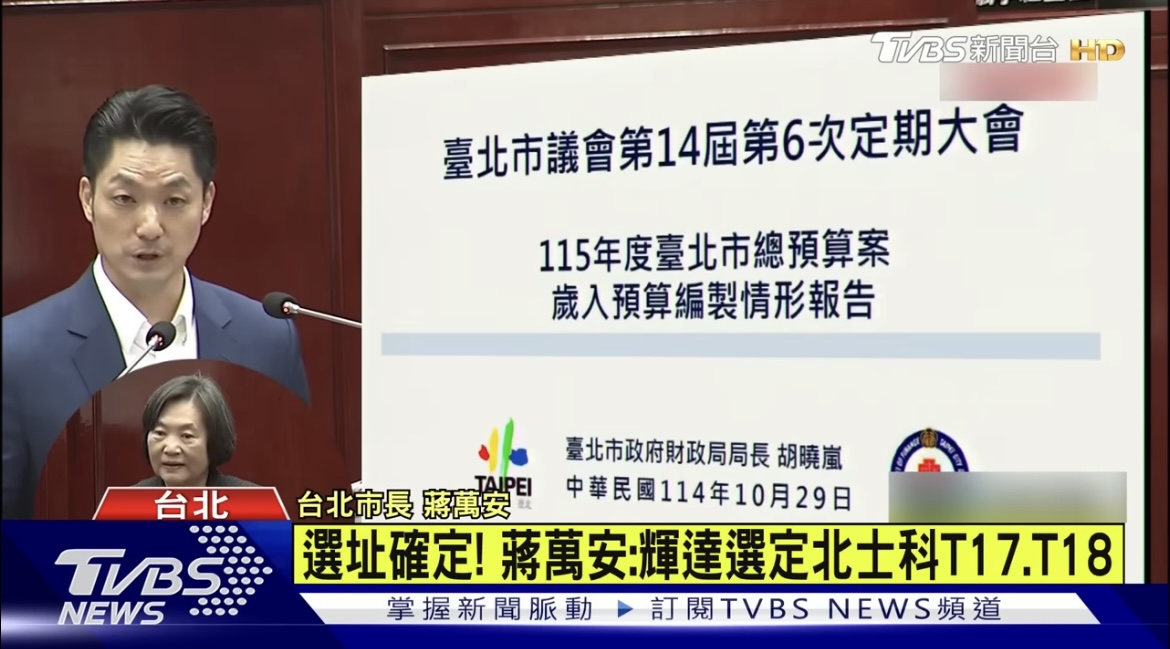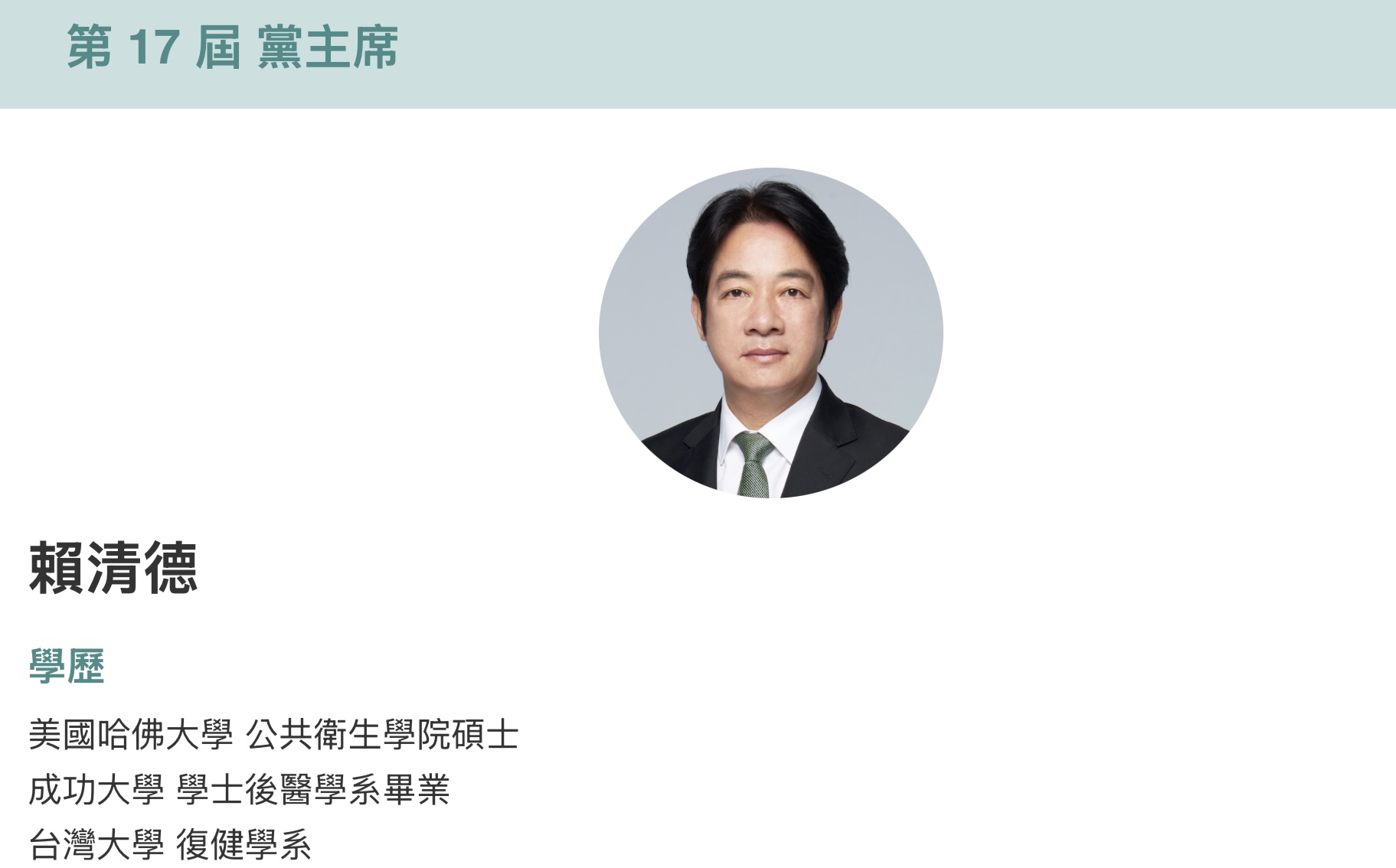照片取自賴清德總統臉書
【聚傳媒上官亂文章】誰能想到,在民進黨「大罷免」失敗後,最需要用「台美共同抗中」來安慰失敗情緒的這幾天,賴清德過境美國的計劃被川普政府拒絕了。這似乎是意料中的事情,因為川普政府正專注於和中國的貿易談判。但是,這對於長期奉行「民主價值同盟」與「抗中遏共」戰略的泛綠陣營,無疑是個雙重打擊。這不僅是台灣對美戰略想象的破滅,更是對過去幾年流行在台灣泛綠陣營、海外反對派之間的「接觸政策失敗論」的一種打擊,他們所信仰的「失敗敘事」,無法再為台灣帶來安全承諾與國際紅利。美國正在用更赤裸的方式衡量全球利益,中國也並未崩潰,台灣的「價值牌」正逐步失效。
在此語境下,「接觸失敗」論在台灣也暴露出其戰略上的盲區。台灣過去一度相信:只要證明中國「失敗」,就能說服美國守護台灣。但川普的舉動說明:美國的戰略邏輯,已不再依賴價值判斷,而是赤裸的利益計算。
川普不歡迎賴清德,並不表示他親中,而是意味著:美國在進入冷戰2.0模式後,台灣只是棋子之一;若台灣不符合其全球布局,便可能被暫時邊緣化。對台灣泛綠而言,這是一次極為嚴峻的現實考驗——他們必須重新理解美國,也重新理解中國,而不是依賴「接觸失敗」來維持道德敘事。
失敗論是幻滅者的心理自救
自從2017年中美貿易戰開始,「接觸政策失敗論」流行起來。對中國少數自由派、部分海外反對派和台灣泛綠知識分子來說,「接觸政策失敗論」是一種心理安置機制,也是一種身份焦慮下的自我安慰。
有趣的是,這些人群曾是接觸政策的共謀者乃至信徒。在1990年代至2000年代,他們普遍相信:市場會帶來法治,法治會帶來民主。這不僅是西方對華戰略的底層信念,也是許多華人知識分子自我理解的核心邏輯。他們與西方建制圈共鳴,堅信中國將在全球秩序中「歸隊」。
然而今天的中國走上了不同的軌道,不但未實現「民主轉型」,反而在全球戰略中展現出更強的制度自信與話語能力。對這些曾經投身「接觸夢」的人而言,這是信仰的崩塌。如果承認接觸政策沒有失敗,就等於承認當年自己的認知失誤,甚至承認:今日的中國,可能正是接觸政策的自然產物。那種精神重負,幾乎無法承受。
當然了,在過去,「接觸政策失敗」也是國內反對派的話語工具,使他們自以為贏得道義正當性,表示自己早就警告過,「我早就說過」,「我」是「看清中共的先知」。這有利於他們在舊語境中維持道德高地與話語影響力。對部分投機者來說,則可以維系過往的資源支持,給對美國內部的強硬派、鷹派提供證據,增強其政策合法性。同時對抗建制派對中國的幻想,否定自由派建制圈對中國長期存在的演化幻想。
因此,「失敗」成了一種必要的敘事形式——用來否定中國今天的成就,進而否定自己當年的選擇,也寬恕自己的判斷。「接觸失敗」成為他們與現實斷裂後的心理自救、道義延續與身份保衛。
泛綠知識分子:將失敗論轉化為戰略工具,卻偏離現實
台灣泛綠陣營在「接觸政策失敗論」的傳播中起到了特殊的橋梁作用。他們一方面與中國自由派共享對民主中國的期待,一方面又必須將自己與「中國失敗」進行政治切割,以維護台灣的主體性。
「接觸失敗」的說法,恰恰提供了一種敘事結構,使台灣得以在國際舞台上自我定位為「另一個中國的可能」,一種民主成功樣本。在民進黨長期執政背景下,這種邏輯也為其對中強硬立場提供道義支撐,使抗中政策不再僅是地緣政治的應對,更是價值取向的體現。
更重要的是,這種論述深度呼應了美國內部鷹派與印太戰略調整。台灣泛綠知識圈將「接觸失敗」作為連接美台戰略的認知錨點,強調過去美國太過天真,如今應更加堅定支持台灣、遏制中國。失敗論在台灣,並不是嚴謹的學術判斷,更多是一種對美關系的談判籌碼。
然而,這也讓台灣陷入一種戰略誤判:認為只要持續強調中國的失敗,就能維持美台之間的信任與合作。然而,現實在變,美國的判斷標準也在變。
如今,川普拒絕賴清德過境美國,標志著一個信號:美國對台政策不再建立在「價值同盟」或「接觸反思」的敘事上,而是更加赤裸裸的現實主義考量。
他或許也想提醒那些深信「民主同盟」與「抗中統一戰線」的泛綠陣營,在川普的戰略中,台灣不過是地緣棋局中的一子,若台灣無法帶來可控的戰略利益,即便你再強調中國失敗,美國也可以選擇擱置。
這也暴露出失敗論的局限性:它只能安慰內部,卻無法影響真實世界的戰略布局。甚至可能遮蔽了台灣面對的真正風險——即在中美之間如何穩住自身的生存空間與戰略籌碼。失敗論無法帶來安全,它只是一種敘事幻覺。
失敗論遮蔽了什麽?
當然,這並不是美國的背叛,而是戰略現實的冷酷邏輯。而當那些反對者們發現,他們既無法在中國獲得話語權,也無法在西方重建意義感,「接觸失敗論」成了唯一剩下的敘述姿態——可以控訴、可以解釋、也可以寬慰自己。
另外,這也是美國內部政治鬥爭的一種表達方式:「接觸失敗」成了鷹派、民粹主義者批判全球化、批判建制派的標靶。當然了,「接觸政策失敗論」還是對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反彈。
事實上,接觸戰略並未失敗於其目標。它確實推動了中國從一個農業國變成了世界工廠,也一度激發了龐大的中產階級、出海潮和信息開放窗口。中國並沒有變成美國想要的樣子,但也不再是毛澤東時代的封閉孤島。
今日中美之爭,不是因為接觸失敗,而是因為接觸成功得太過頭了。中國之所以遭遇遏制,不是因為它不夠開放,而是因為它強大到了超出西方制度和心理邊界的承載力。
失敗論之所以流行,不是因為它是真的,而是因為它滿足了太多人的情緒需求與道德焦慮。它成了一種情緒命名、一種敘事自救,也是一種避免面對現實的方式。它在中國異議者、台灣泛綠、美國建制自由派之間流動、放大、共鳴,仿佛是普世價值的最後據點。它能解釋中國為何不可理解,也能為「我們沒能改變世界」找到替罪羊。
但真正需要問的是:如果中國並未失敗,只是走向了另一個現代性?如果美國也不再在乎自己和台灣是否夠民主價值?如果台灣不能靠敘事爭取支持,而必須靠實力與布局維持安全?或許,是時候放下失敗這個詞,用更覆雜的視角去看這個已經改變的世界了。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投稿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