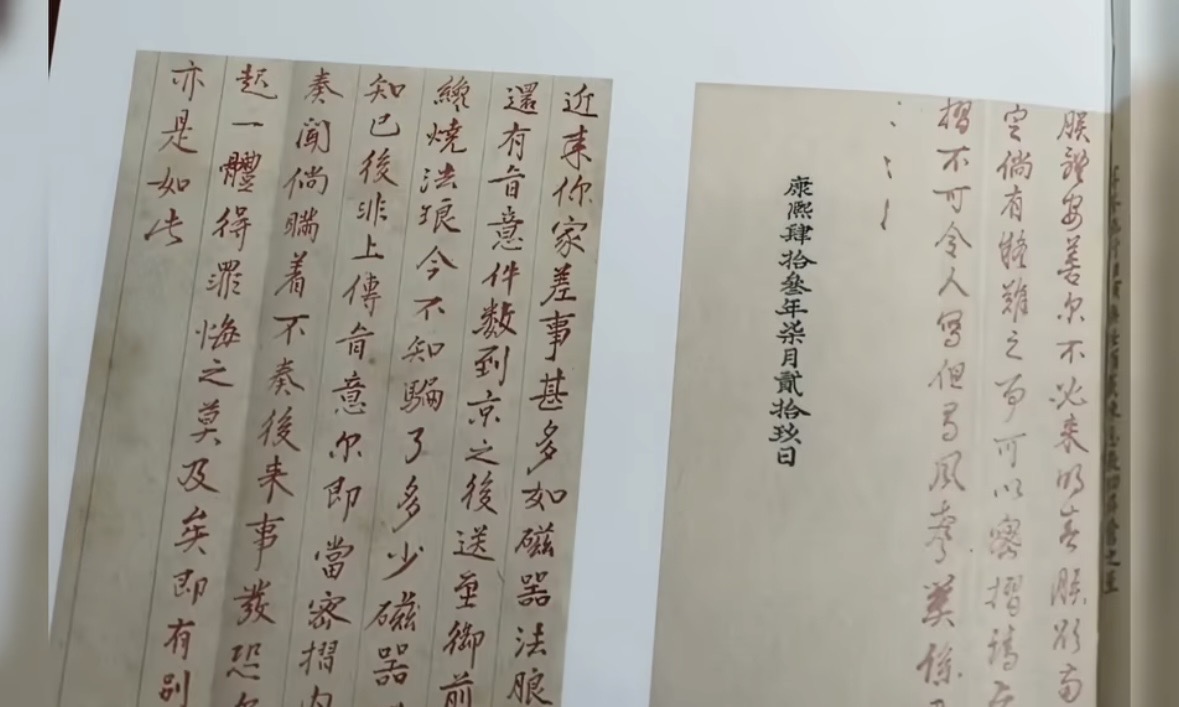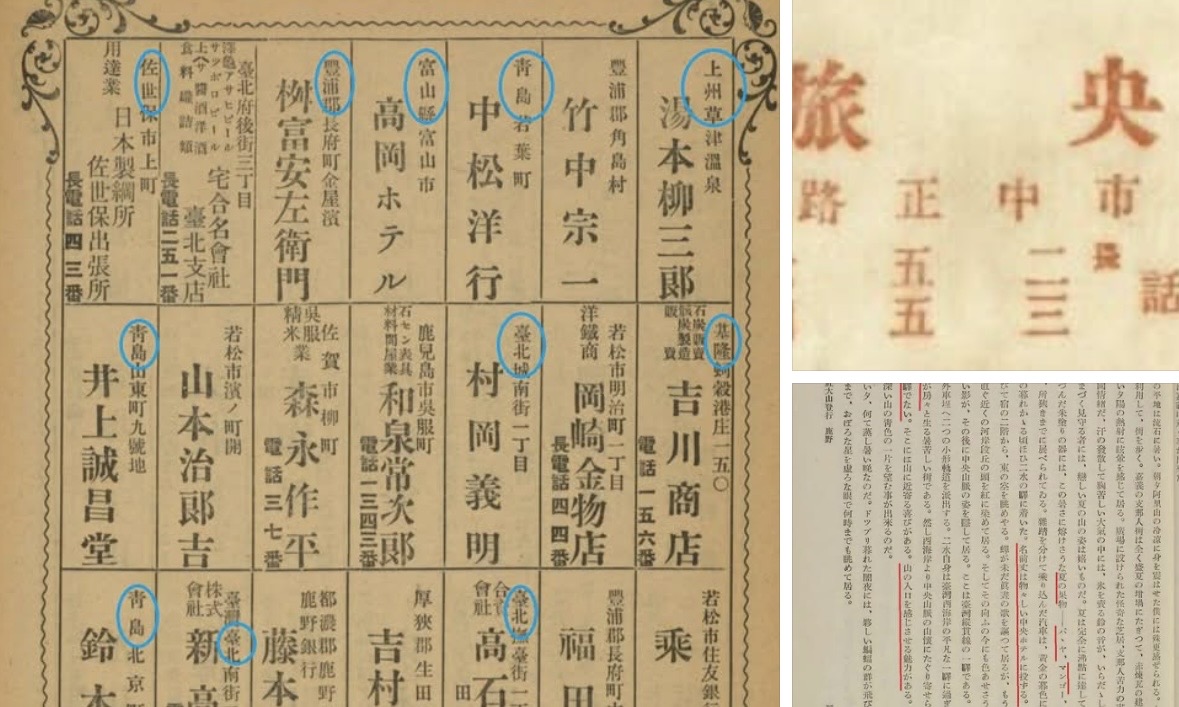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蔡詩萍專欄】欣賞馬友友在國家音樂廳的「凱基雋永饗宴」(YO-YO MA Solo Live in Taipei),過了快一個星期,才稍稍能靜下心,回想這場盛對我的激盪。
這一星期,病懨懨了三天,事情又多,頗有稍縱即逝的無奈感。但或許也因為如此,反而在回想馬友友那晚的表現時,懸蕩出某種很特別的感受。
本來,當晚我最直接的印象是:馬友友的體態呈現年紀了,但他沉浸於樂曲的神情依舊是那個自年少便成名的馬友友,以他現今的年歲,他遊刃有餘於琴弦的撥弄指尖的彈跳,簡直算出神入化了!體態的隨日月而佝僂,又算什麼呢!
可是,這幾天,我自己身體不舒服,連帶被迫請了一兩天的假,百無聊賴之際,有時連書也看不下,書稿亦不想整理,賴在床上呢,輾轉反側幾小時便受不了了,乾脆直接耍廢,什麼都不做,懶洋洋自己。
微恙期間,我在想:像馬友友這等世界級演奏家,行程滿檔,為了不辜負樂迷的期待,為了避免樂評家的尖銳評論,他肯定「連生病放假都是很奢侈的想望吧!」
雖然我明白,任何行業裡頂尖的A咖,一樣也是「要日常生活的」,於是,在馬友友家居的附近,非常有可能許多民眾會有機會看見他出門散步,吃餐館,逛超市,等等。日常即永恆,常見他的人,是流淌於同一條時光之河裡,不易感覺他有什麼變化。
但,對我們這些,僅能偶爾在演奏會的殿堂上,遠望他的樂迷,他的變化,就往往是數年,或更多年以上的間隔了!
這樣的間隔,往往會讓我們訝異:啊,偶像怎麼也老了呢!但我們卻同時忘了:不是偶像也老了,是你我,我們也都在這數年一見,更多年一見的間隔裡,跟著老了。
光陰似水,但水流依舊,是曾濯足於其間的我們,被時間推著往前走了,從少年,從青年,從中年,走到了老年。
我們如此,偶像們,能不如此嗎?但A咖之為A咖,偶像之為偶像,披星戴月,兼程而進的他們,若能不被時代淘汰,若能不被粉絲遺忘,他們就得不斷的在日常裡精進,在自己成名的絕活裡日精月益。
新人必然輩出,但老將必須伏櫪,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故事,每一代人亦有每一代人心儀的偶像。
偶像會老,但偶像逆時而行的自我惕勵,畢生把一件自己擅長的事做到極致,做到藝術般的境界,做到不負少年頭的初衷,對我,就是極為感動的啟示錄了!
那晚,馬友友拎著大提琴出場,瞬間,我嚇了一跳:怎麼間隔了多年,他顯老態了。但,當他坐下,閉目,睜眼,持弓的右手,撥弦的左手,先後啟動,琴音瞬間劃破音樂廳裡的沉靜,或許還有驚訝於他有點老態的狐疑,霎那間,「熟悉的馬友友」回來了!
劃破時空,劃破台上的他與台下的我們不知不覺走過的時空歲月,我們「都靜止在當下了」,一個由馬友友大提琴為我們靜止的當下。
我不是重度古典樂迷,馬友友當晚的曲目顯然也未刻意討好久違的觀眾,巴赫一連串的無伴奏大提琴組曲,你只能非常專注的,聚精會神的聽。
但獨奏會結束一個星期了,我在病懨懨,在忙碌的節奏裡,竟時時會浮現馬友友瞇著眼,似笑非笑的沉迷於獨奏的神情,人生也許最終都是無伴奏的時候才可能真正俯視自己吧。
謝謝馬友友。讓我們看到了,人會老,但完美的境界,永遠都在;年少的初衷,始終年輕。
作者為知名作家、台北市文化局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