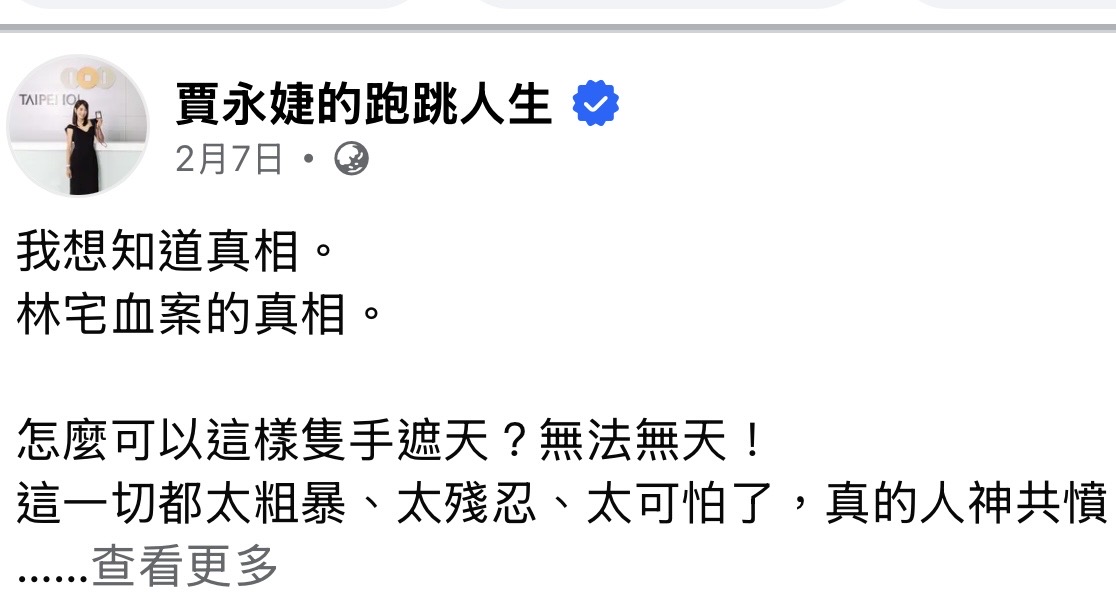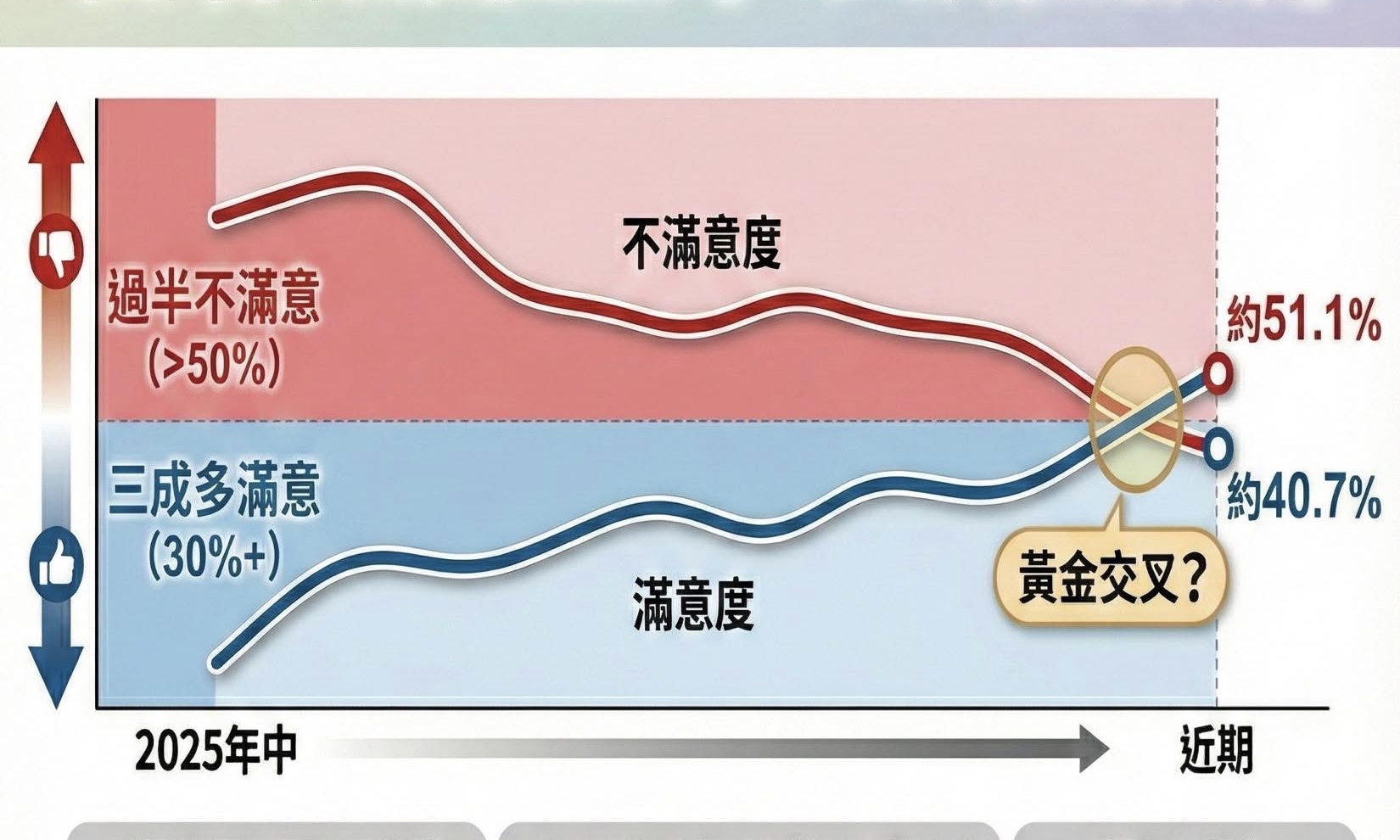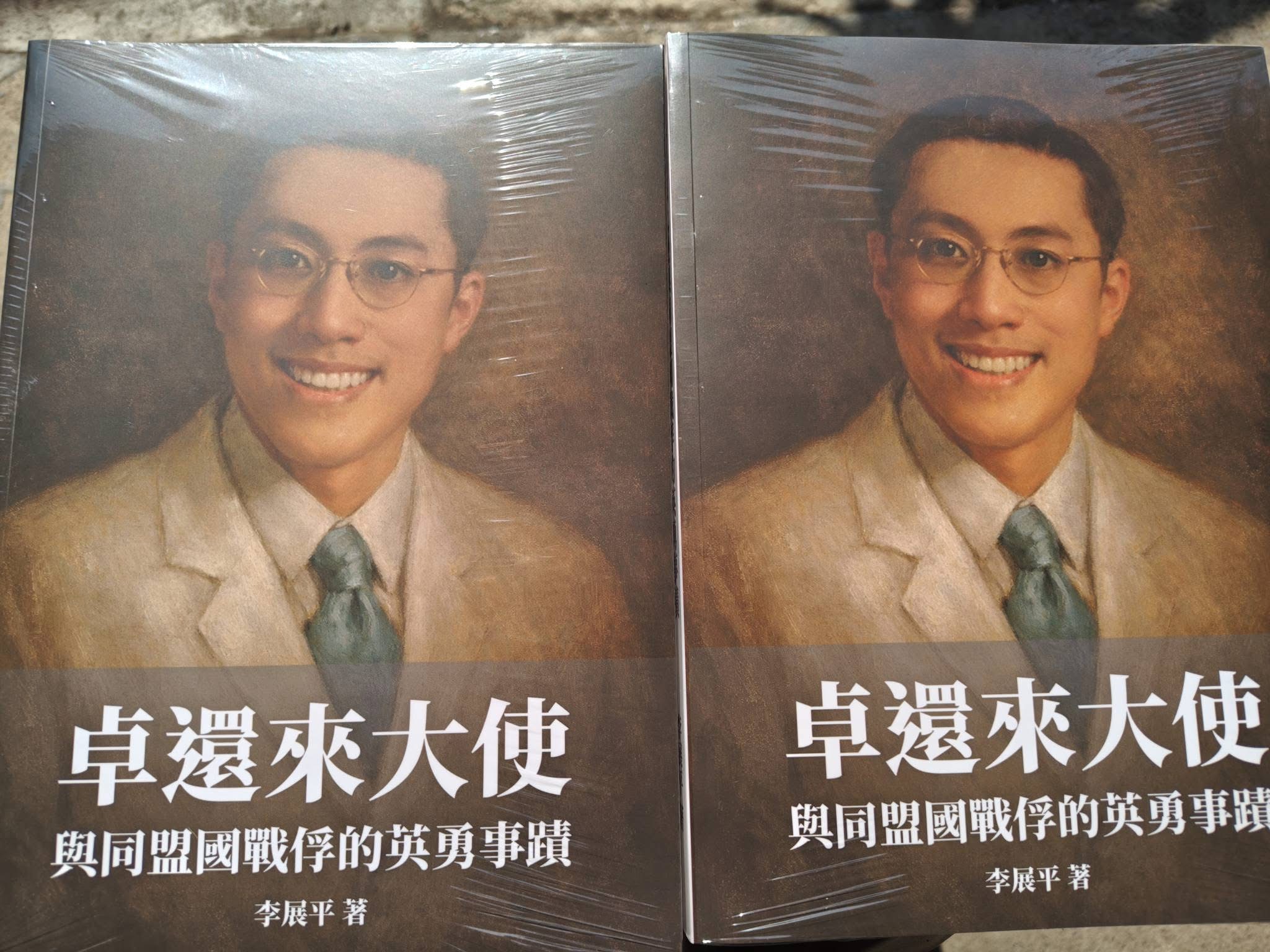照片為美國白宮官方肖像照
【聚傳媒奔騰思潮專欄】前聯準會主席伯南克、葉倫等近50位美國跨黨派知名經濟學家,近日聯名要求美國最高法院否決總統川普的全球關稅政策。他們指出,此政策基於對全球經濟的誤解,貿易逆差是經濟常態,並非川普政府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IEEPA)所稱的「非比尋常、異常的」威脅。他們強調,「對等關稅非但無法處理貿易逆差,反而將對經濟造成數兆美元損失,衝擊遍及每一州與家庭」,這事經濟學入門卻深遠的道理。
當總統聲稱可在未經國會具體授權下,憑藉一部意在「緊急」時期授予巨權的法案,對幾乎所有進口商品徵收對等關稅,其憲法合法性勢必引發激烈爭論。川普政府主張依據1977年《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以國家面臨緊急狀態為由,直接對全球多國進口商品徵收互惠關稅。此政策不僅涉及對外經貿,更觸及憲法核心問題:誰擁有徵稅與貿易規制權?
美國國際貿易法院與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均認為,川普政府以IEEPA為名所徵關稅超越總統法定權限,屬於違法行為。聯邦巡迴法院批評此舉權力過度膨脹,徵稅範圍無限。川普政府不服上訴,最高法院擬於2025年11月初快速審理。此案判決將對總統權力、國會授權及憲法分權關係產生重大宣示作用。
本案對美國憲政與未來行政權擴張具深遠意義。在重大議題原則、憲法結構與分權原理制約下,即便最高法院由保守派掌控過半,全面支持川普在IEEPA下徵關稅的主張難以圓理。最高法院較可能作出折衷判決,授予總統有限、針對特定情境的關稅權力,否定其全面大規模徵稅主張。
美國憲法第一條明確賦予國會對徵稅及對外貿易規制的專屬權力,總統並無一般課稅權或變動關稅權。若總統欲對進口商品加徵關稅,須有國會事前通過的法規或授權。傳統上,總統在外交、國防、國安或緊急情況下雖享有較大裁量空間,但其行使權力,尤其是具重大經濟或政治影響的政策,仍須建立在明確國會授權基礎上。模糊授權將削弱國會在財政與貿易政策的核心角色與問責監督功能。
川普政府主張IEEPA授予總統「管制」進口及「調整」進口交易之權力,但該法案從未明文提及「徵稅」、「關稅」或「徵收進口稅」。在此文字框架下,法官解釋時通常反推:若國會未清楚授權,不得將徵稅權轉授行政部門。此即「明示授權原則」或「清晰陳述規則」的思路。若總統主張在IEEPA下徵收廣泛關稅,法庭須面對疑問:國會是否曾默許此種重大課稅權力下放?若無,該主張易被視為越權。
IEEPA最初為冷戰時期經濟制裁與外國交易所管制設計,旨在賦予總統於國家遭受外國經濟威脅時宣布緊急狀態,並對涉外經濟交易進行管制。該法實務上主要運用於資產凍結、進出口禁令、金融制裁等措施,極少用於課徵關稅。過去總統若欲對進口徵稅,多援引具體貿易法案(如《貿易擴展法》第232條、第301條等),這些法案具較明確程序與國會監督機制。IEEPA未在立法歷程中被明確用作關稅工具,因此法庭有充分餘地拒絕擴張其關稅含義。
此外,IEEPA本身對總統權力設有限制,如總統每年需向國會報告、必須聲明為「處理異常且非常的威脅」,且法案行動應限於該威脅範圍內。即使總統擁有緊急權力,也須在「應對特定威脅」與「威脅因果關聯」間保持合適比例,否則易被法院以「超出授權範圍」推翻。挑戰IEEPA關稅案除重大議題原則外,尚可從「與緊急威脅的切合度」與程序合憲性角度檢驗。
下級法院實踐中,國際貿易法院已於2025年5月判決,認定川普政府以IEEPA徵收的「世貿性與互惠性關稅」及以芬太尼、移民等議題為由徵收的「Trafficking Tariffs」皆屬不合法。法院認為IEEPA未授予總統如此寬廣關稅徵收權,故行政命令應撤銷。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也認為,IEEPA中「管制進口」授權不涵蓋關稅徵收,因課稅與管制是性質不同的權能。
即便行政法傳統上對模糊授權存有解釋彈性,近年最高法院在許多具重大經濟與政策影響的行政行為中,已逐步採用「重大議題原則」作為憲法解釋工具。該原則主張:針對具深遠經濟、政治效應或跨部門影響的重大政策決定,除非國會有極為明確授權,法院應拒絕將該權力默認給行政機關。
重大議題原則的核心理由在維護國會在重大公共政策上的主權、避免行政部門越權濫用,及防止行政部門以解釋模糊法案為由擴張自身。在IEEPA關稅案中,這些關稅牽涉進口配額、跨國貿易關係、對美國消費者與企業成本影響、財政收入分配與國庫負擔等,顯然屬「重大議題」範疇。若最高法院接受此原則,對川普政府全面支持關稅權威的主張將構成極大法理障礙。
法理層面川普關稅案存重重障礙,但預測判決須檢視最高法院構成、個別大法官立場傾向及司法哲學走向。目前最高法院由9位大法官組成,保守派佔6人多數,自由派3人。
保守陣營雖傾向給予行政機關較大空間,但不代表對總統濫權完全開綠燈。在行政法、憲法結構與分權原理問題上,即使保守派法官也常強調限制行政濫權與維護國會主導地位。涉及重大國家政策、外交與貿易案件時,最高法院過去常以「法理」為檢查行政權尺度,而非僅依賴政治傾向。
本案中,首席大法官羅伯茲及巴雷特、卡瓦諾被認為最具關鍵性。這三位法官在制度中軸上的決定,往往比其他大法官更具實際影響力。若此三人傾向對總統徵稅主張設限,最高法院很難全面背書。何況最高法院近年在行政法領域判案傾向,已有「限制過度授權」、「強化國會授權清晰性」趨勢(如應用重大議題原則、削弱Chevron deference等)。由此而言,即使保守派法官也習慣在權力擴張主張前保持警覺。
若最高法院真正接受重大議題原則作為行政審查核心工具,將直接對川普政府主張IEEPA徵稅構成阻礙。法院可能認為川普關稅政策屬「前所未見」、「具重大影響性」、「與國會立法傳統不一致」範疇,故需國會極為明確授權才能成立。此類分析在學界與評論界已被普遍認為是對川普主張最具殺傷力的法理解釋方式。法院或會拒絕行政解釋論作為支撐總統主張的論據。
適用重大議題原則時,最高法院可能劃設「例外空間」給予行政機關在特定國安、緊急情況下有限度權力,但例外須有清晰邊界、與國會授權相稱。換言之,最高法院可能不會像下級法院完全否定總統制定關稅的可能性,而是給予「有限且受監控」框架。因此,即使最高法院有意給予行政機關空間,也極不可能無條件全面肯認川普主張的每一項關稅徵收。
最高法院很可能採取折衷式判決,既限制總統權力,又保留一定空間,並劃設明晰界線與標準。具體而言,法院可能判定IEEPA本身未明示授權總統對所有進口商品徵稅,更不應賦予總統可長期廣泛徵稅權力;此類無限制徵稅違背國會授權清晰性要求與重大議題原則。同時,法院可能承認,在特定國家安全、外交或緊急威脅情況下,總統可在限定時期與範圍內運用IEEPA授權實施關稅措施。
川普政府以IEEPA為依據推動大規模對等關稅,是憲政結構與行政權範圍邊界上的重大賭注。若最高法院接受其主張,意味行政權進入近乎無限擴張道路;若予以全面否定,則可能引發財政、市場與制度強烈震盪。在目前制度與法律脈絡下,全面支持此權力擴張幾乎不可能成為最高法院首選路徑。法院較可能採取折衷式裁判:限制總統在IEEPA下徵稅範圍,僅允許在特定緊急、國家安全情境下有限度行使,並要求與國會報告、監督、時間與對象限制等機制配套。
最高法院判決不只是對川普政策的判斷,更是對未來行政權、國會授權與憲法分權體系的重塑。此訴訟可能成為美國憲政秩序的里程碑。法院若能在判決中適切劃定界線,為緊急權與立法授權間的張力設下制度性節制,美國或許能避免邁向「君主式」行政體制;若法院選擇放任行政擴權,則憲法秩序堤防將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