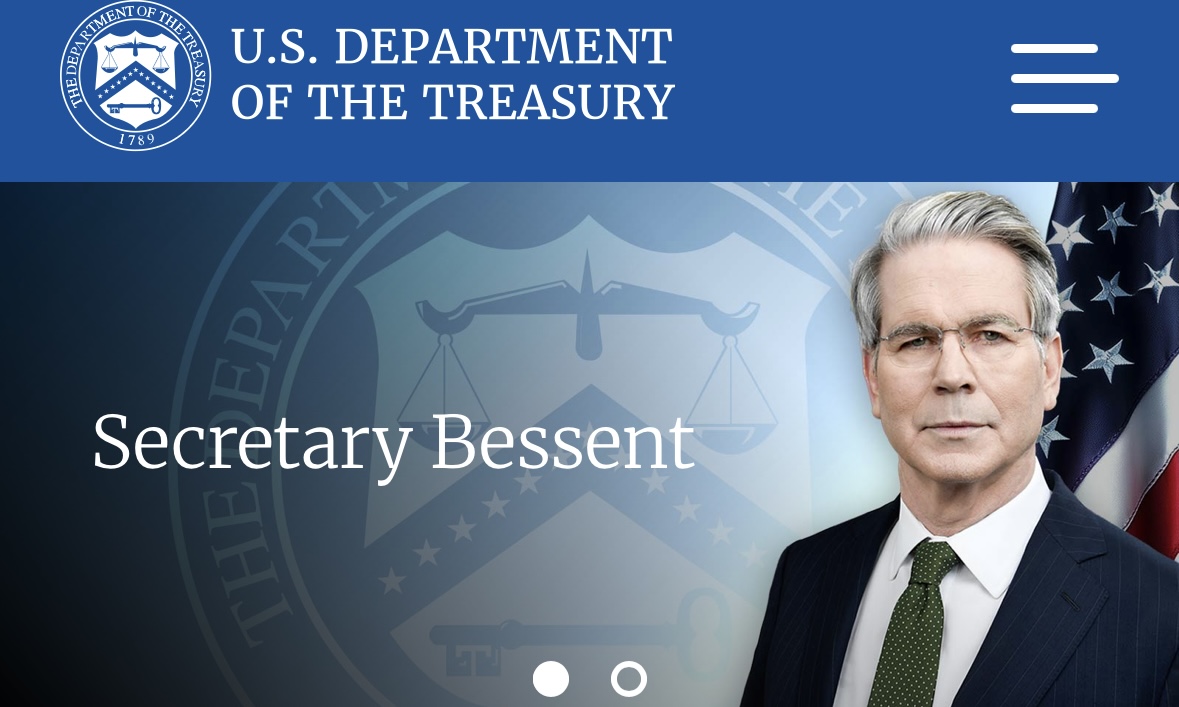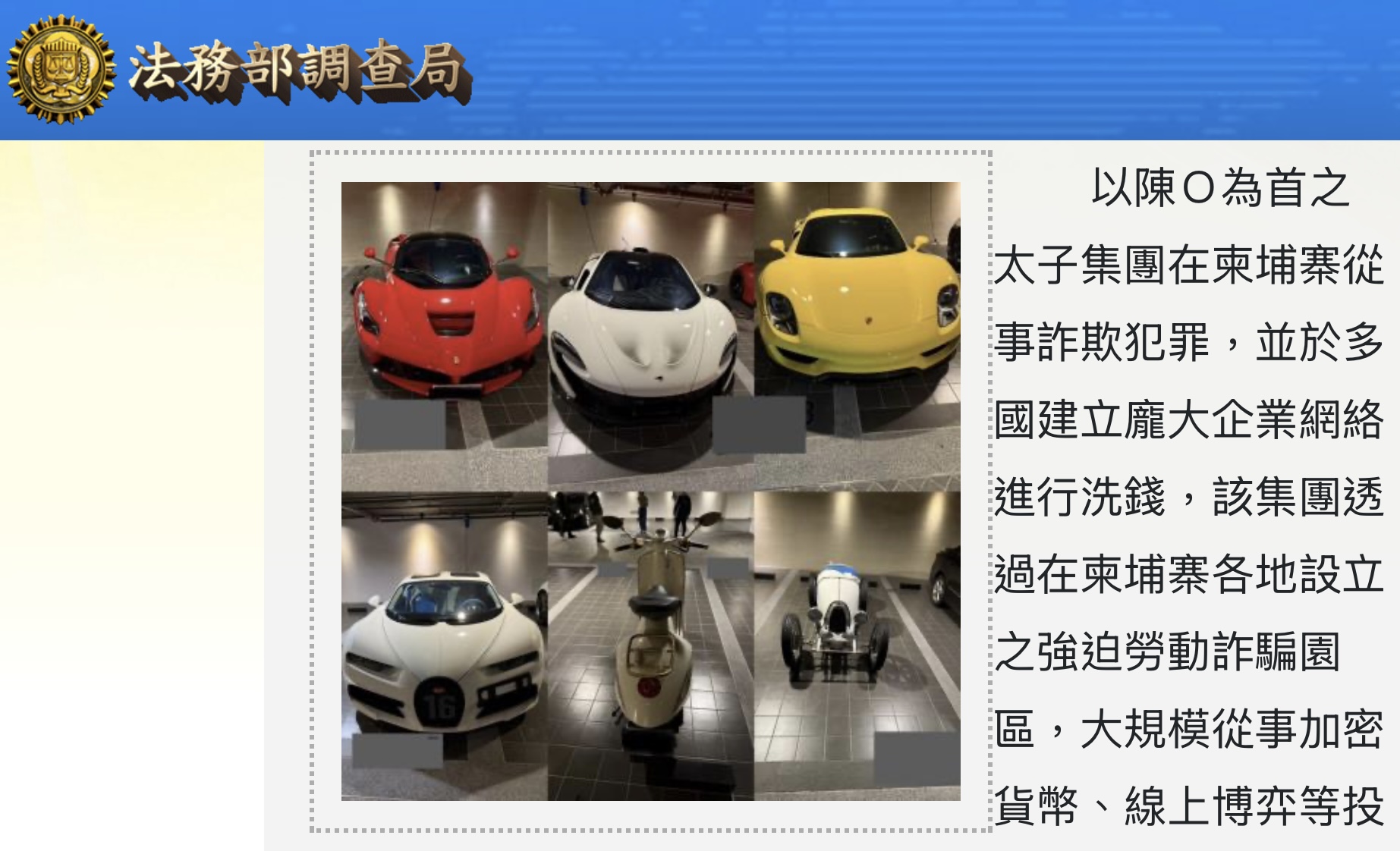照片為美國財政部官方網站
【聚傳媒奔騰思潮專欄】美國38萬億美元國債正逼近臨界點。高盛執行長大衛·所羅門罕見以「清算(reckoning)」形容當前局勢,警告若經濟增長無法顯著提升、政府仍以現行速度舉債,美國終將面臨全面財政重整的時刻。
債務暴增與經濟依賴的惡性循環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國債從10萬億飆升至超過36萬億美元,增速超越任何歷史時期。疫情刺激、基建擴張與軍費支出構成長期性的「結構性赤字」。所羅門指出,美國財政刺激已深嵌於經濟運作,形成「舉債依存模式」。若以現行利率再融資,總債務突破40萬億只是時間問題。
他強調,應對危機的根本不在於單純增稅,而是提升經濟增速—若能將平均成長由2%提高至3%,將可逐步消化債務;否則,利息與支出將吞噬未來財政空間,使美國陷入自我束縛的黑洞。多位經濟學者發出同樣警報。哈佛教授肯·羅格夫指出,美國「應急空間」極度有限;歷史研究顯示,當國債占GDP比例過高,經濟成長顯著下滑。
橋水基金創始人瑞·達利歐則在「大債務周期理論」中指出,美國正處於長達50至75年周期的末端,此階段通常以貨幣貶值與債務重組收場。他將當前情勢比擬為二戰前夕—美元體系或將迎來一次結構性轉折。
「溫水煮青蛙」的財政墮落
2000年時,美國尚有財政盈餘,國債僅佔GDP的55%。然而連串戰爭、減稅與危機救助計畫使赤字急速膨脹。如今赤字成為制度化現象,主要有三項危險信號:
1.債務增速超越經濟增速。十年間國債年均增長逾7%,名義GDP僅約4%,如同收入停滯卻持續刷卡的人。
2.利息負擔惡化。2023年美國利息支出達6590億美元,首次超越國防開支,嚴重擠壓教育、科研與基建投資。
3.債務周期逼近終點。若循歷史模式,美國或將面臨債務重組、貨幣貶值或信用體系重建。
債務警報全面響起
目前美國聯邦債務已超36萬億美元,占GDP比重達120%,遠高於二戰後峰值。IMF研究顯示,當債務比率超過100%後,每上升10個百分點,年均成長減少約0.2%。未來若利率維持現水準,2030年光利息支出可能突破1.2萬億美元,超過所有可自由支配開銷總和。
更嚴峻的是「信心滑坡」。外國央行對美債的信任正下降,其持有比例由2008年的55%降至約30%。中國、日本等傳統大買家紛紛多元化配置。2023年債務上限危機更令惠譽將美國主權評級降至AA+。這些事件揭示,市場對美國財政信心正在慢慢鬆動。
若危機爆發,衝擊鏈條或成系統性崩塌。首先是「債務螺旋」:為還舊債借新錢→利率上升→利息支出再擴大→被迫縮減支出或加稅→經濟放緩→稅收下降→再次舉債。如此循環難以止息。
其次是債券市場風險。美國國債規模約25萬億美元,是全球債市核心。一旦失序,將迫使全球資產重估。摩根大通執行長傑米·戴蒙直言,美債市場可能「裂開」,波及全球金融體系。
若政府選擇印鈔還債,將引發貨幣信任危機。2022年9.1%的通膨率證明:當市場懷疑美聯儲維持幣值的能力時,通膨會自我強化,進入惡性循環。
在社會層面,削減福利與增稅勢必加劇階層矛盾。從2011年「占領華爾街」到2020年種族衝突,美國內部分化已多次被經濟壓力點燃。政治極化與社會不滿的交互作用,使治理難度急劇上升。
最終,美元霸權若被侵蝕,全球金融秩序將重構。美元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地位,是美國最大的戰略資產;然而金磚國家近年致力推動本幣結算與非美元化儲備,此消彼長的態勢已初現端倪。
化解危機的可能路徑
1.控制赤字與優化支出
多數經濟學家認為,將財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內,是重建穩定的底線。依國會預算辦公室模型,若能維持該水準,至2050年美國債務比率可穩在150%左右,雖然仍很高但可控。改革重點包括:削減軍費(現逾8000億美元)、優化醫療支出(占GDP17%)、堵塞稅收漏洞(每年損失約6000億美元)。但這些改革都將觸及龐大利益網絡,需要前所未有的政治共識。
2.以增長化解債務
真正的解方是經濟成長。投資基建、AI、綠能、教育與人力培訓,被視為提升生產力與國家競爭力的關鍵領域。若平均成長率由2%升至3%,未來十年美國經濟可增加約5萬億美元產值,產生足以抵銷部分債務壓力的增長紅利。
3.優化債務結構與貨幣政策協同
政府應延長國債期限以降低再融資風險,目前平均期限僅6年,若提升至8至10年可顯著改善流動性風險。美聯儲則須在控通膨與護增長間精準拿捏,避免緊縮太多致衰退或寬鬆過早再通膨。
4.穩定國際信用與制度透明
維持美元信任需加強財政透明度與對外溝通,例如建立定期的債務風險報告、與主要債權國協調政策、強化全球金融安全網機制。唯有讓市場確信美國有能力且有意願償債,才能穩定其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核心地位。
避開斷崖命運
美國當前正站在財政與信用的十字路口。長期依賴舉債與貨幣寬鬆的政策紅利已到盡頭。未來十年將決定其是否能以制度改革與產業轉型穿越債務黑洞,或陷入貨幣貶值與社會撕裂的惡循環。
「清算」不僅是財務結算,更是一場國家契約的測試。若美國無法以理性與遠見面對這場債務現實,其全球領導地位或將進入長期調整期。倘若能在危機中完成政策重構,則仍可藉創新的力量與制度韌性,再度撐起世界經濟的樞紐。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