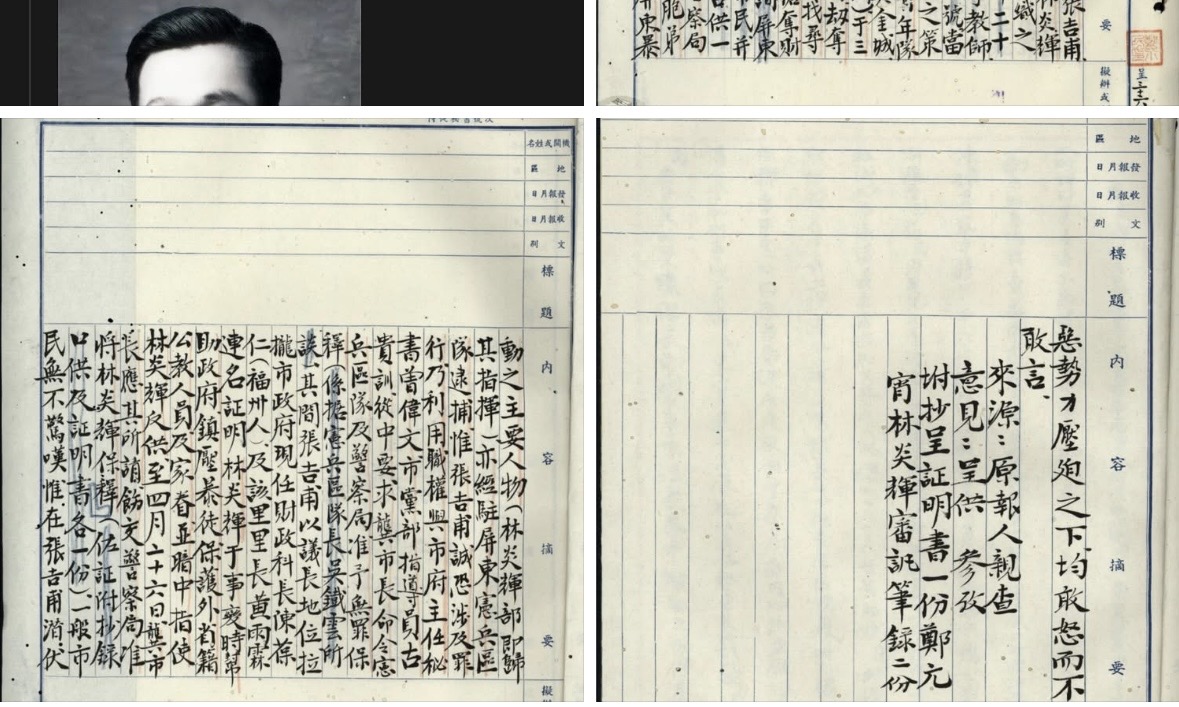十指紅蔻丹的美蘭姨媽對於我兒時來說,相當於一號傳奇人物,雖然她是母親的長輩,我們應該叫姨婆,但是跟著母親叫慣了,我們也都叫她姨媽。
一提起她,陳伯的浙江腔會講:「劉美蘭很拉風!」稱美她半屏山外加大墊肩的衣著形象,父親的山東腔多說:「劉美蘭是有辦法的人!」頌揚她人脈八面玲瓏;對母親而言:「阿蘭姨對我有恩。」指她改變了她半生,並且驚訝,姨媽重度嗜辣,說起話來若何還能那般吳儂軟語,艷羨她回印尼之頻繁「袂輸行灶腳」。
母親原於印尼棉蘭出生,外公當地經商趕上好時機,發財好一陣子,極盛時期僱用四位管家:洗、熨衣、二廚(大廚係外婆)、保母、打掃、洗盤,各司其職。然守成艱難,母親14歲那年,外公遭人倒會僨事,財去樓空,一家大小最後被迫搬家。
運命中途淘汰她大小姐的身分,打回原形,一部分記憶一直停格在那不堪的原鄉離散相錯,兩棟花園洋房遭查封,一部賓士、一輛富豪、一台偉士牌只得拋售變現,一家十幾口老小搭東方女王號,七層樓高的日本豪奢郵輪離開,船上泳池、酒吧、精緻餐飲全與他們無涉,別人度假,他們跑路。
海路三天兩夜落腳雅加達,外公改做油漆工,舉家租屋一處換過一處,根本失根浮萍。姨媽就在彼時結識開小吃店謀生的外婆。
先後離緣印尼兩段婚姻,姨媽嫁來台灣。輾轉獲知母親後來碰上愛情騙子,遭一名日裔印尼人棄若敝屣,一介弱女子要獨力扶養私生子實屬大不易,她順勢媒合想討老婆、生孩子的退伍老兵老王,為母親說媒,牽成這門跨海親事。
同為天涯邊緣人,母親跟父親皆有類似飄零遭遇,來台時無親無故,故鄉路斷。好在母親有姨媽,從旁關照順應初來乍到的身份,乃至產後做月內,或介紹其他印、華新娘當朋友,互遣悲懷。
姨媽四海之內皆姊妹,當初協助父親辦理收養哥哥的手續,親自帶母親由香港轉機飛印尼領人過來;香港三日,借住她朋友家,維多利亞港夜景、可口叉燒、狹仄民房,人情熙攘的香江回味。
姨媽情路亦是一波三折,同台灣第一任丈夫離婚作收,換母親反過來安慰她,女人同盟的概念。失婚大齡女,男人緣不減反增,年近花甲,梅開四度,最終黃昏之戀情定另一老兵老朱。
西門町長沙街一段,國軍英雄館軍友餐廳大宴來客,席開20桌,父母親、陳伯、哥哥與我都是座上賓。緣於某任前夫是代天宣化宮廟神職人員之故,她精讀《三世書》,曾鐵嘴直斷哥哥前世褻瀆神佛,今生四肢難健全;卜算我天生「孤佬」而長壽,讓我耿耿於懷。
姨媽家住台北市中正區南端的富水里嘉禾新村以南,浴廁既乾且淨,散發著一股不刺鼻的淡雅芳馥氣息,以後才曉得那是只有百貨公司才買得到的資生堂紫羅蘭香皂。
客廳不管時總有好多印尼的魚、蝦餅、千層糕等南洋氣息的點心零嘴,閒吃不盡,她更習慣於留訪客於自家用膳,視餐前告辭為大忌。
眼見大人們廚房忙進忙出,我們這些小輩等待饕饗她的飯菜香,芳鄰雞犬之聲相聞,活脫一座擁擠的樂園。她家還有燕窩、雞精、養命酒等補品,永春街的小日子過得滋潤。姨媽與母親相聚放大原鄉情結,總說印尼哪裡好,笑鬧道我長大乾脆討印尼太太。
週末假日,兩家三代經常一同上陽明山、烘爐地、烏來郊外踏青,或流連中華商場、光華玉市、來來百貨。
姨媽三位孫女我都要叫姊姊,她們最愛搔我腳底板,把我逗得不要不要的;偶有哪個小孩鬧彆扭,她軟言調停;誰突然發燒,她掏出隨身常備藥。尚有小時家裡豢養的家犬吉利,原是姨媽長女的狗兒,見我珍愛牠,大度慨贈。
她大女兒老來得子,卻不意兔唇,她叨唸:「一定是有身的時墫,烏白剪物仔放佇咧眠床頂,去剪到囝仔的嘴。」迷信歸迷信,倒也透過正規醫療手術盡量修復。
姨媽插金戴銀,一雙花藝巧手則表現在擺銀柳,客廳叮叮咚咚一瓶掛滿金黃喜氣吊飾,外婆、母親見狀,歡喜其背後銀兩、黃金寓義,隨後仿效跟進,在農曆年討喜應景,靜候花苞處迸開似貓尾巴,年也差不多過完了。
那時候並不懂什麼叫貴婦,或許住嘉禾新村南邊也絕無可能是世俗標準的上層社會,但我感知她是這樣的方方面面俱到,跟每個人保持著又親密又疏離的分寸;而且若缺她拉線搭橋,可能也就沒有我。
何奈,某年某月某一天,姨媽一家便不再和我們往來。其後還曾要共同認識的人傳話給母親說:「麥擱見面!」母親聞言,一時錯愕、惱火兼而攻之,真的賭氣把姨媽的住址、電話等聯絡資料作廢。
這段悠悠漫長空白歲月,無日無之。直至前年底初履寶藏巖,突然惦記起不遠處、類似氛圍的永春街,竟也就沿路摸索找了回去,這才明白姨媽家原來係菟絲花般寄生眷村的違章建築群。儘管富水里拆禿一大塊,屬違建的姨媽家反倒依稀猶在,一問里長,方知她已飛天告別紅塵,享壽80好幾。
母親事後懊悔不已,估計是生了什麼誤會,說不定家族某某私下向姨媽有借無還,甚或不排除傳話者加油添醋了,當時姨媽一定只是說說氣話,怎想到這一當真,竟是生別離。
從前鐵齒,並未認定她替我們兄弟倆所算的命,四年前哥哥因工傷意外瘸了腿,住院治療下肢,孰料加碼再驗出口腔癌末,未幾病故。而我,已能轉化與生俱來的孤僻習性,手寫我口,口訴我心,借文字傾吐難以言傳的心事,安身立命。她的先見之明,多年後逐一應驗成真,竟成我們的後見之明。
人生路,實難有一段永不走樣反形的關係。離少聚多,不可得;好聚,尤其不好散。幸得回憶像鐵軌一樣蔓延,鑿通時間與空間,路長情更長。
美蘭姨媽至今仍是我心中的一則傳奇──永春街不凋萎的一枝花。
●經授權刊載,原出處為王景新同名部落格。
●本文為投稿文章,不代表i-Media 愛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