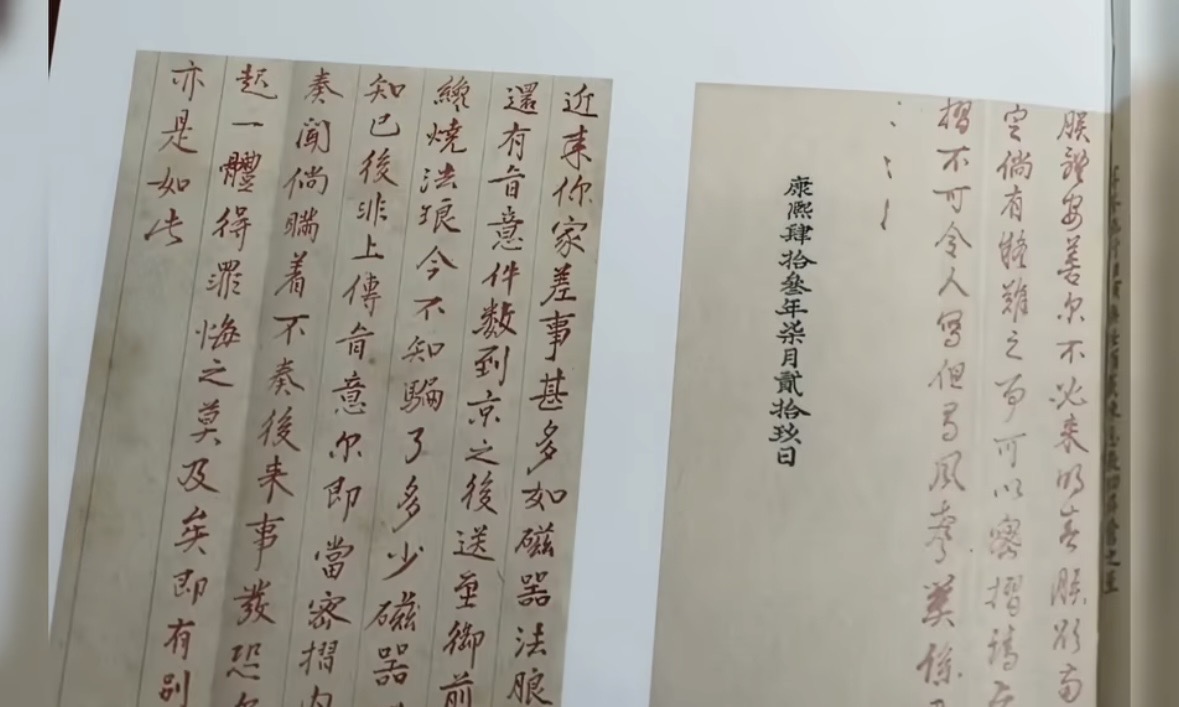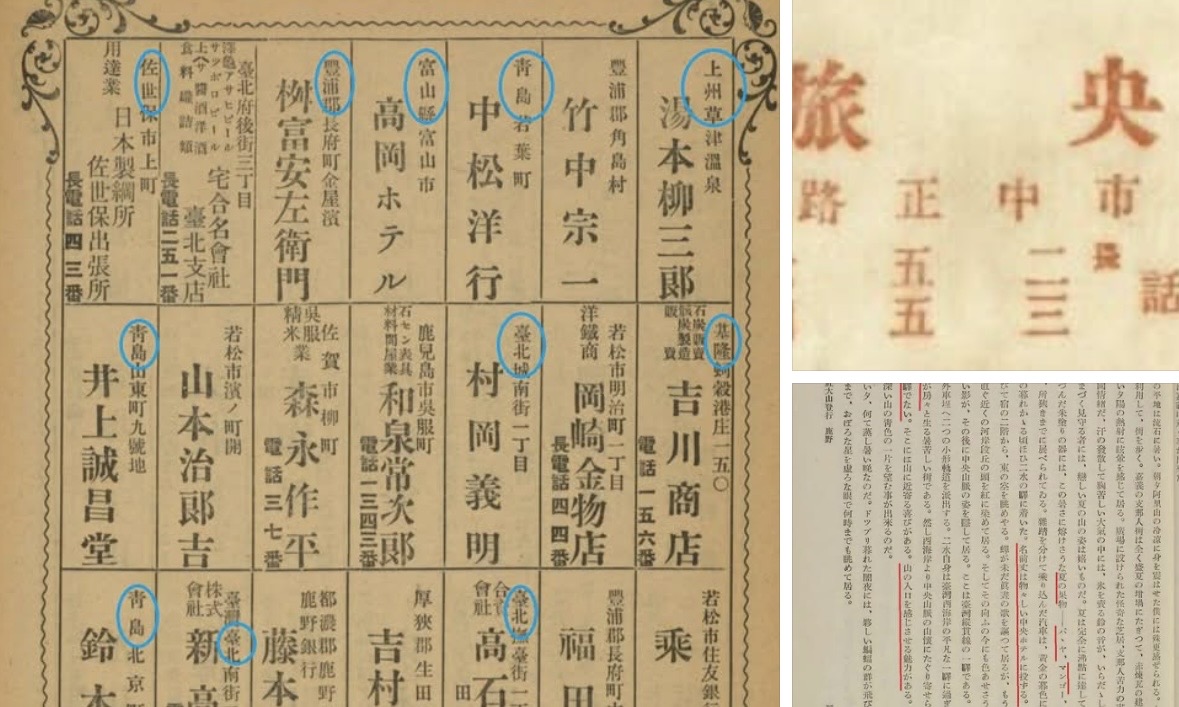照片為作者提供
【聚傳媒蔡詩萍專欄】我必須承認,父親去後百日了,我不是常常想到父親。
並不是我不想他,或我不難過,而是,他九十八歲了,我很清楚,他平靜的過去,於他是好的,於我們家人是充滿感謝的,他陪了我們,這麼久。
但我想到他的那些時刻,都很具想念的儀式。
比方說,我剛剛想到他,是我在後陽台晾衣服,當我彎腰拿出衣物時,眼角瞄到陽台外,不遠方的天空,藍得發亮,幾抹白雲白得出奇,那一刻間,我想到父親。
我很想跟他說:爸爸您好嗎?正在清風徐徐的草地上,吸煙,想我們嗎?
白雲靜靜飄著,天空繼續藍得出奇。
想到他的時候,我停下晾衣的動作,靜靜望著那幾抹白雲,發癡著。
樓下路邊有不知名的母親,叫喚著她的女兒:不要騎太快喔,下坡時手要按住煞車。
她的女兒笑著回答:我知道啦!
音聲甜美,陽光燦燦。
這麼一個平淡的週末上午。這麼一個尋常的時刻。
這麼一個讓我突然想念父親的瞬間。
這麼一個似乎讓我可以理解父親對我的愛的神秘連結。
我笑了。父親應該靜靜的,坐在他的墓碑前的台階上,安安靜靜的吸煙吧!
我於是彎腰,再拾起洗衣機裡剩下的衣物,一件件晾起來。
我完全沒有父親教我騎車之類的記憶,應該是沒有,也絕對沒有。
我的單車記憶,是隔壁鄰居的哥哥,把他的單車借給我和他的弟弟,我們兩個便在村子裡的較寬的路面上,你扶著我,我扶著你,從不會上車,慢慢練到可以歪歪扭扭的騎上路。
因為家裡沒單車,我並不確定父親什麼時候才知道我會騎車。
我女兒的單車記憶一定有我。我買了一部單車,帶她去車行自己挑樣式,挑顏色。
我載她去住家附近河濱的停車場,平日車不多,場地夠寬夠大夠長,不怕她妨礙他人,不怕他人妨礙她。
我扶著車尾,她踩踏踏板,父女倆常常在那廣場上耗掉整個下午,然後,載她去買冰飲,我喝咖啡,父女倆隨意有一搭沒一搭的聊著。
練車當然要選好天氣,既然天氣好,想必天上一定有雲,一定有藍天,間或,也會有風,一陣陣的吹過河濱的草叢,吹過那小小的溪流,吹過我們父女倆滿身大汗的身軀。
我不會記得那麼多關於女兒練車時的天氣,但我想像中的幸福,我實際經歷的幸福,必然是父女倆在陽光下,笑嘻嘻,驚呼呼的喧喊,與對話。
細節早忘了,但女兒會騎單車這事實,是真實的存在。
我與父親相處的很多細節,我大概不記得的必然十之六七吧!
也一定是這樣,我們做孩子的,國中高中起,就進入自己的世界,現在的孩子掛起耳機,隨手打game ,拿起籃球,找了球伴,霎時就進入自己的世界。我那年代,我那家庭環境,我進入自己的世界,是進入閱讀,當然也會進入籃球。
我挑一本書,週末去住家附近的小山上,一個人坐在那,默默的讀,或默默的,望著遠方,胡思亂想著。
若是去打球,必定打到天昏地暗才肯回家。
我父親望著我,不說什麼,最常說的是:去洗澡吧,洗好來吃飯。
我回想這些畫面,有時還會忍不住淚濕。
他是沉默的父親,他是寂寞的父親,但我們是孩子時完全不懂,只是覺得有距離,有鴻溝,他跨不過來,我們跨不過去。彼此僅是對望,其中有真情,但少了真正的體諒。
等我長大了,等我在職場上,在社會上,稍稍闖出點名號,我忙,他老,我更忙,他更老,直到他生病了,我們方驚覺:啊,時光或許不多了。
但他常常體貼的說:沒關係,你們忙啊,你們忙。
但再忙也要陪陪他吃飯啊,散步啊,隨意聊聊啊!
只可惜,他更老了,老到精神不濟,老到記憶隨處亂跳,我們的對話因而無法完整。
我父親一定是很愛我們的,他節儉成性,他眼神凝望,他容忍孩子,他在晚年會不時拍拍我,說我讓他很驕傲。但我太像他了,常常不懂怎麼溫柔的回應,只會說:啊沒什麼啦,沒什麼啦!
現在想讓他拍拍我,亦要在夢中了。
洗完衣服,我到女兒房間,輕輕推開門,望著她熟睡的臉。
我把稍稍未關緊的窗簾輕輕拉闔,讓一室的幽光繼續維持夜晚的氛圍。週末,讓她多睡一會吧。
我不確定女兒知不知道我進她房間,幫她拉上被子,闔上窗簾,撿拾該洗衣物的畫面。
但我是記得一些父親進我房間,輕輕看我是否安睡,被子是否蓋好的畫面。
但我常常假裝睡著了。這使我在年歲漸長後,不免感覺自己的不安。然而父親總是容忍了。
容忍必定是親子關係裡最神聖的踏板,使得鴻溝,使得距離,在多年後,會在我們心有愧咎的每一刻間,立即一塊塊鋪成愛的殿堂,抵拒時間的削蝕。
父親過去後,我不是常常想到他,但只要一觸及我對他的思念,便彷彿穿透了神秘的空間,我們父子對望,對視了。
像那片藍得出奇的天空,那幾朵白的鮮明的浮雲,我望著,望著,父親便浮現了。
想念何須常常。我們心底懸一條思念的繩索,想要時,便去攀爬。
作者為知名作家、台北市文化局長
●專欄文章,不代表J-Media 聚傳媒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