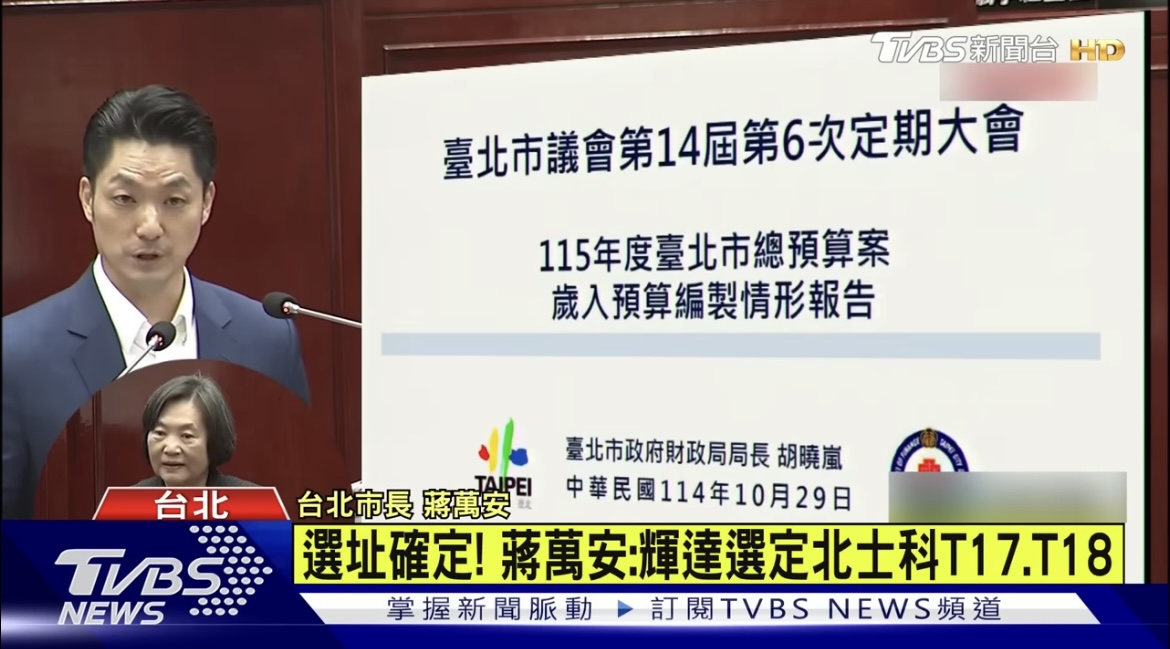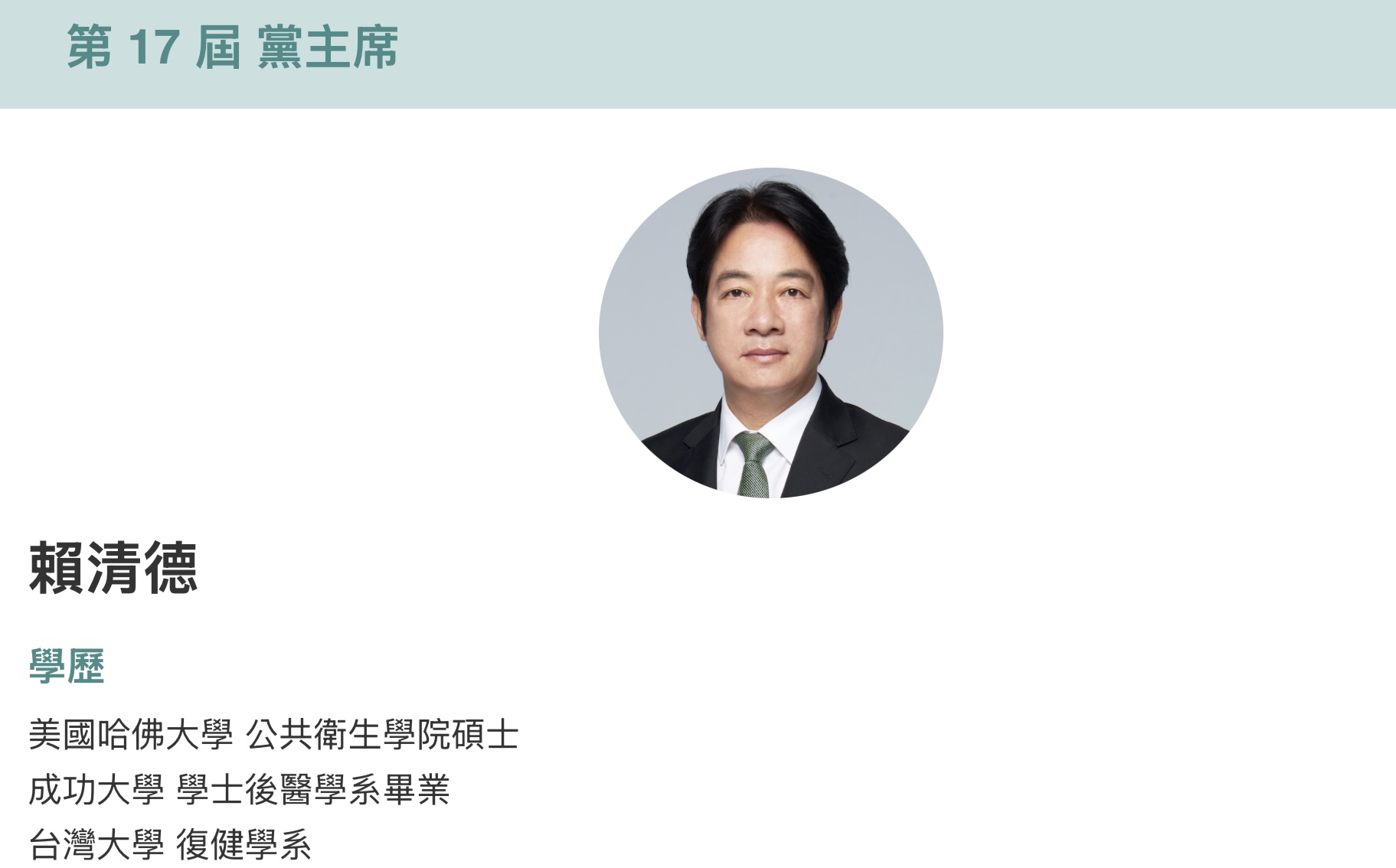照片為《紐約時報》官網截圖
【聚傳媒上官亂文章】龍應台今年在《紐約時報》的4月發文《台灣維持和平與自由的唯一途徑是與中國和解》,當時在台灣引起了廣泛討論。9月16日,她再次在聯合報發文:《為何我們今天要談和平》。兩篇下來,龍應台的和平論述脈絡逐漸清晰,如果說《紐約時報》篇是大框架的定調「和平優先於對抗」,《聯合報》篇则是操作層面的展開:如何以韌實力與戰略主動性推動和平。
聯合報文繼承了紐約時報文的論述,又進行了极其關鍵的補充。這篇文章不僅直面了當時的爭議,更突破了很多台灣當前公共語境中最敏感、最容易被汙名化的問題——「談和平是不是賣台」「和平要不要等中國給」「和平是不是天真幻想」……她將這些禁忌正面攤開,這是非常重要的突破。
聯合報文到底補充了什麽
龍應台在紐約時報《台灣維持和平與自由的唯一途徑是與中國和解》那篇文章裏用了諸多現實生活切片闡述和平觀點,可以簡單提煉為三點:幾乎所有台灣人都希望守護自由,這點沒有分歧;但分歧在於實現方式——是透過與中國和解,還是選擇對抗;在對外關系方面,台灣需要再思考:單純依賴美國、同時拒絕並對抗中國,已不再是可行的道路。最後她提出真正的擔憂,沒有先確保和平,就不可能真正維持台灣的民主。
在當時如火如荼的「大罷免」運動氛圍下,文章當然引起軒然大波。但沒想到,近期,她再次在聯合報發文《為何我們今天要談和平》。這篇文章不僅直面了當時的爭議,更突破了很多台灣當前公共輿論的禁忌。
主要觀點如下:
兩岸政治話語的悖論。在實力巨大懸殊的情況下,台灣領導人也比照對岸,聲稱「維護和平」,但真正手段都是「強軍」,這其實是以戰爭語言包裝和平。
和平比戰爭更困難。戰爭容易煽動情緒、製造恐懼和悲憤;和平則需要理性、自製、同理心和智慧,因此「主戰是糖果,主和是苦藥」。
歷史的借鏡。和上一篇的生活切片不同,這篇文章她聚焦歷史,以北愛爾蘭、以巴、德法、南非的例子顯示,認為和平往往靠「強者的謙卑」,而不是靠軍力比拼。和平不是慈善,而是強國最有利的投資。
主張「和平」才顯示台灣的主體性。她認為把「和平」全丟給中國決定,其實是否定了台灣的自主。台灣不能只是等待中國變化,而是要主動設計自己的和平路徑。除了兵推,台灣還要做「和平推」,主動把和平當作戰略籌碼。
和平是戰略選擇和國家風險管理。她一再呼籲,和平不是天真幻想,台灣要主動布局,以創造國際空間、避免沖突、爭取時間。
「韌實力」是台灣的籌碼。台灣在晶片、數位信任、公民社會等方面都有優勢,這些軟實力可以成為溝通和建立信任的「柔性武器」。
總之,她認為,目前台灣應該理性看待「和平」與「戰爭」的話語陷阱,和平不是軟弱或退讓,而是台灣對未來的主動選擇與投資,並且,應該透過主體性拒絕長期以來的「受害者心態」。
直面敏感與禁忌,打破語言陷阱
在《聯合報》文章裏,她特別提醒民眾別被口號迷惑。戰爭的代價遠超和平,強國若只依賴武力,最終只會導致孤立、撕裂與復仇循環。當然,她不是否認軍力,而是強調 單靠軍力無法換來和平。
最重要的是,是她這次直面了很多在台灣當前語境下的諸多禁忌問題:
「和平即』賣台』」?首先,在目前台灣公共語境裏,談和平的人往往被貼上「親共」「賣台」的標簽。這是一個現實的禁區,她把它正面提出,甚至以被愛爾蘭為例,提出過去那些率先主張開啟對話的人,也被認為是「賣國者」,千夫所指,萬人踐踏。
「和平要去跟中國說」?很多綠營的論述認為,既然威脅來自中國,那要和平就去要求中國,不必在台灣內部談。她反擊:這樣說等於否認台灣有主體性,把決定權拱手讓人。
「中國不可能給和平,所以談和平是天真」?她點破這種說法的邏輯陷阱:如果台灣只等待中國民主化或政權崩潰,那就意味著台灣完全放棄了主動性。
「和平靠軍力」是否只是另一種戰爭邏輯?她指出賴清德的言辭幾乎是習近平的「鏡像」,以台灣之力在以軍備來定義和平,結果是火球對撞。她質問:比軍力是台灣的優勢嗎?
「和平是天真幻想還是戰略籌碼?」她提出一個激進觀點:和平不是退讓,而是主動籌碼,是台灣可以投資、設計的戰略選擇。
龍應台的留白以及突破
當然,對兩岸和平問題,大眾還有一些疑問,在這篇已經足夠坦誠的文章裏,依然還找不到答案。
比如:和平路徑的具體設計。她強調台灣要「主動設計和平路徑」,但具體是什麽?是恢復兩岸對話?開展民間交流?提出中立化方案?還是推動某種國際多邊機製?她沒有展開。
台灣如何面對巨大的軍力懸殊。她批評「唯有軍力換和平」的邏輯,但也承認軍事實力「重要」。但「多重要」「如何平衡軍力與和談」,她沒有具體權衡。
社會內部的撕裂如何解決?她提出台灣內部「恐懼、分裂、標簽化」的問題,但沒有具體方案如何改變這種輿論氛圍。單是一個二二八的記憶,台灣社會就已經難以彌合。
另外,她指出歷史上和平往往靠強者的謙卑(德國、法國、南非),但台灣不是強者。她沒有回答:小如台灣,如何真正「主導和平」?
對於這些「禁忌」的問題,作為一個作家,她的處理方式更多是「提出問題,改變視角」,而不是給出具體方案。但是這樣,仍然可以迫使社會正視「和平」與「戰爭」之間的復雜張力。——當然,也更可能是因為現實上確實沒有一個現成答案。在當下,沒人敢承諾自己能給出具體的政策藍圖。
她只是用語言的解構,迫使社會去直視那些被簡化為口號的邏輯陷阱,進而開啟禁忌式對話,讓台灣社會能夠承認:和平不只是屈服的同義詞,而是一種必須主動思考、設計、投資的戰略選擇。這種突破,本身就是當下台灣政治語境裏極為罕見的勇氣。
作者為作家、媒體人
●投稿文章,不代表聚傳媒J-Media立場